2024年05月28日晚,西北大学玄奘研究院读书会第88期活动在线上顺利举行,此次读书会主题为:读阿斯曼《宗教与文化记忆》——导论、第一章。分别由西北大学哲学学院硕士生张立与文学院硕士生杨舒主讲。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谢志斌副教授,西北大学历史学院、文学院、丝绸之路研究院等院系相关专业博、硕士研究生及北京大学、南京大学、同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南开大学、厦门大学、吉林大学、苏州大学、华东理工大学、华南师范大学、贵州大学、中央民族大学、上海师范大学、天津师范大学、北京舞蹈学院等各高校学生,共40余人参加了此次活动。此次活动由东华理工大学中文系讲师、硕士生导师米进忠博士担任评议人,历史学院博士生肖雪锋担任主持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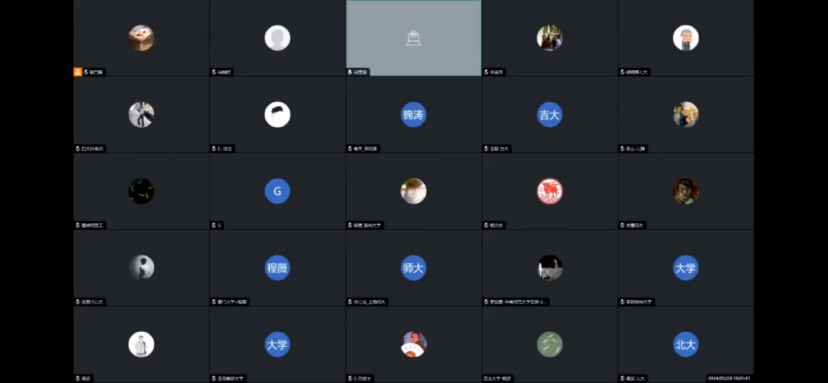
硕士生张立将《宗教与文化记忆》——导论,分为五个部分进行了详细的导读:第一部分,简单介绍了扬•阿斯曼夫妇为20世纪80年代西方“记忆潮”中“文化记忆”研究的代表性人物,《宗教与文化记忆》是一本将过去和现在链接起来,讲明文化文本和国家认同重要性的理论读物。第二部分,对“文化记忆”的学术史脉络进行了回顾,分别从哲学、心理学与非哲学、心理学(如:社会学、人类学、历史学等)三个视角介绍了学术史上的先辈、思想理论与著作等,进而引出了扬•阿斯曼夫妇“文化记忆”理论构成的四个基础:尼采、帕格森等前辈思想;源自涂尔干,成型于哈布瓦赫的“集体记忆”理论;阿比•瓦尔堡作为“文化科学”的“图像学”的延伸;皮埃尔•诺拉认为的“记忆之场”。第三部分,首先,阐释了“文化记忆”理论的两个维度,文化理论视角与记忆理论视角。分别介绍了主观意义、结构意义、拟剧意义与制度意义等四个不同意义的文化概念,扬•阿斯曼作出明晰的神经维度、社会维度和文化维度,或说神经结构、社会作用和符号媒介等,三个记忆层次的划分。其次,就是解释著作中“集体记忆”、“交往记忆”与“文化记忆”三个概念与相互的联系。说明扬•阿斯曼看来,哈布瓦赫提出的“集体记忆”实质是“交往记忆”,而“文化记忆”则是对“交往记忆”的拓展与延伸。“交往记忆”在交往互动中是易逝的、分散的,其延续性不强,因而“文化记忆”将过去具有奠基性意义的历史事件,通过文本系统、仪式系统、意象系统等外在的、客观的文化符号载体进行保存、固化和延续,同时依据当下社会环境的需要、兴趣和利益等对记忆进行调整和重构,使其始终保持与集体成员紧密的情感关联。最后,总结了“文化记忆”的连续性、重构性、政治性、道德与伦理性等四个特性。不同于以往“记忆”与“传统”有明确的边界,而扬•阿斯曼认为“记忆”与“传统”是有重合性的。“文化记忆”连续性的连续与断裂之间,存在着其重构性。不认同档案只是信息沉淀与复述重写,而是具有可塑性的建构行为,因而“文化记忆”才可以成为连接过去、现在与未来的“中介”。政治性则延伸于列维•施特劳斯的热、冷社会模式的思想。将向过去的、具有读写能力且在国家形态中的高级文化分析为“热的记忆”,其对社会具有刺激作用。将跟宇宙关联且带有口头传统的部落社会中的记亿文化分析为“冷的记忆”,其对社会具有镇静作用。说明功能记忆与储存记忆的划分,背后指向的是“文化记忆”的道德性与伦理性。在社会情境的发展中,功能记忆与储存记忆不断地进行互动,才构成了“文化记忆”内部的动态机制,即双重记忆模式。第四部分,介绍了扬•阿斯曼的《宗教与文化记忆》里常用的符号与文本分析、口述史和民族志分析、比较历史分析、定量分析等四种研究方法,并分别指出各研究方法存在的风险与运用路径。第五部分,张立同学提出了四点自己的问题与思考:认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概念的研究,存在着客观史实及主观记忆与认同的两个路线;社会变迁与“声誉记忆”,会受到情境性视角与能动性视角影响而变化;或许,在学界“记忆”研究中,“记忆”一词或存在概念泛化的倾向;认为记忆、叙事历史与时间四大主题的重合性也值得注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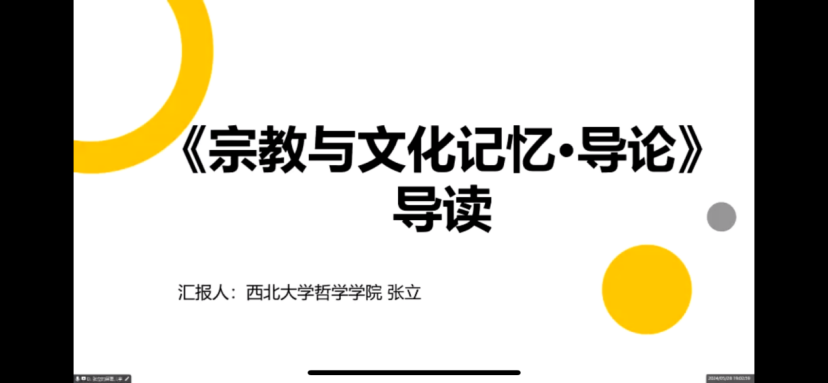
第二位进行汇报的是硕士生杨舒,她的汇报内容为第一章—无形宗教与文化记忆。她将汇报分为六个部分进行介绍。第一部分,介绍了扬•阿斯曼提到的卢克曼的“无形宗教”概念,及“无形宗教”致使宗教概念内部分化为“IR”和“VR”,即分别为:更高的、无形的宗教,能决定个人和社会、“世界”的关系;与特定祭祀机构和祭祀制度中具体可见的宗教。第二部分,是扬•阿斯曼认为与“IR”和“VR”相类似的古埃及文化的介绍。扬•阿斯曼发现古埃及文化中的“玛阿斯”(Maat),即普遍和谐原则,最高抽象层面上的有意义的秩序的总和,与“IR”的概念接近,即“埃及三角”模式,就是将法律(道德和政治的世界)与祭祀膜拜仪式(宗教的世界)对立又融合在一起。并介绍了“次级宗教”的概念与它将“宗教世界”提高到终极存在的等级,取消了不同层面的“IR”和“VR”的区别的作用。而扬•阿斯曼认为,卢克曼的无形宗教理论是对重新引入区别的呼吁。第三部分,是“文化记忆”的转变。“文化记忆的神学化”,成为了废除“IR”和“VR”区别的主要驱动力(“统一的”或退行性宗教的起源)。而在这一过程中“文化文本”的形式在这一世界观中被客观化、持久化、熟练化。“文化文本”又以“规范的”和“形成的”两种形式存在。文字的出现使“文化记忆”历史分为两个阶段:基于仪式重复的阶段和基于文本重复的阶段,从仪式到文本的连贯性转变绝不仅是单由文字促成的,至关重要的是采用了所谓的“经典化”的原则。经典化历经无文字社会的符号化和仪式循环;“传统流文本”;“经典化和解释”三个阶段进入下一阶段。第四部分,扬•阿斯曼提出,经典化的过程也是社会分化的过程,即分离出一个独立于政治、经济、司法甚至宗教权威的职位,而其任务就是解释或关注文本的意义。“典范的文本”需要一个第三方,一个文本和受众之间的解释者,只有在文本、解释者和听众的三角关系中才能呈现其意义。第五部分,是“文化记忆”的去经典化和分化、现代的类“埃及三角”结构的介绍。在现代,宗教的权威和垄断解释(VR)正在人们的世界观和对意义的终极理解(IR)方面失去控制力,VR和IR的分离再度浮上水面。出现了类似“埃及三角”的结构,哲学、艺术、科学及所有独特的价值领域一方面构成世俗的范围,另一方面仍然能进入替代品和民间宗教的级别,因其仍被笼罩在IR之下。第六部分,杨舒同学提出了三点自己的问题与思考:认为应要明确分析,扬•阿斯曼与伊利亚德理论上的区别和相互的关系;扬•阿斯曼的现代“埃及三角”与保罗•蒂利希对宗教辩护之间的对比;以及思考“IR”和“VR”模型,是否与中国传统宗教类型的适用。

接下来由本次读书会的评议员米进忠老师,对两位同学的汇报进行了点评。首先,对两位同学内容、逻辑、理解与思考能力给予了肯定,并认为两位同学在原作的基础上,有自身的分析与运用理论的做法难能可贵,与中国本土的适用性的尝试分析更是精彩。同时认同“西大大学玄奘研究院”,阅读宗教经典并面向公众汇报的培训学生研究能力的模式。其次,米老师谈到了他本人读后的两点感受:第一,扬•阿斯曼提出的“文化记忆”概念,在思考“人”本身,扬•阿斯曼认为,人的本质是一种存在,存在的根本表现是“文化记忆”的存在,因此,他的观点是人的本质就是“文化记忆”。扬•阿斯曼提到过,“文化记忆”理论是“传统本体论”转向的一种形式。作为“人”的社会性,在历史传承中以文化形式传播,即文化的传承表现在人的存在的身上就是“文化记忆”。扬•阿斯曼的谈论已超越了种族、民族等的界限,因此是从普遍意义上的人、从人的本质、人的存在来谈论“文化记忆”,这也是他思考“文化记忆”的出发点。第二,是学术方法的借鉴意义,提倡同学们要形成学术史意识,在先辈学者的基础上进行对学术的推进;概念的意识,提取概念,归纳命题;比较意识,注意要与身边资源进行比较与相互观照。最后,米老师分享了自身宝贵的学术经历,勉励大家培养客观中立的研究立场,作为宗教研究者,在研究、写作过程中必须反复反省自身,形成平视研究的态度;深入浅出的学术表达能力,拒绝故弄玄虚,理解要深刻,表达要清晰、了然。要求反复咀嚼、解读经典,逐渐提升抽象思维能力,进而提高学术分析能力。对于即将在学术研究领域,入门或入门有困惑的学生,米老师建议,定质、定量阅读有兴趣、权威的学术论文,并与“写”、“谈”、“听”结合的方法。活动结束之际,两位汇报的同学对米老师的点评表达感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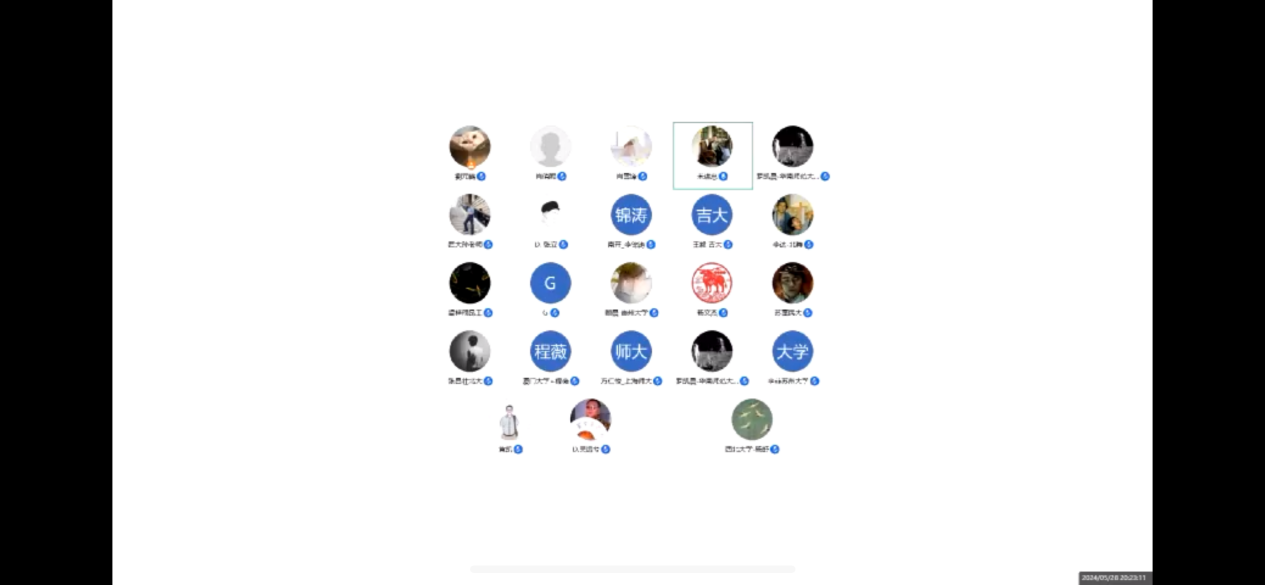
至此,西北大学玄奘研究院第88期读书会圆满结束。
(编辑:李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