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0月15日晚7点,西北大学玄奘研究院读书会第95期活动在线上举行。本次读书会的主题为:“读韦伯《印度的宗教》第八~十三章”,领读者为西北大学历史学院硕士生郭佳琪和华也靓,由中国政法大学哲学系副教授孙国柱老师评议。西北大学李永斌副教授、谢志斌副教授,上海大学人文学院黄凯老师,以及西北大学、山东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四川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师范大学、贵州大学等高校和单位的20余名师生在线上一同参与了此次读书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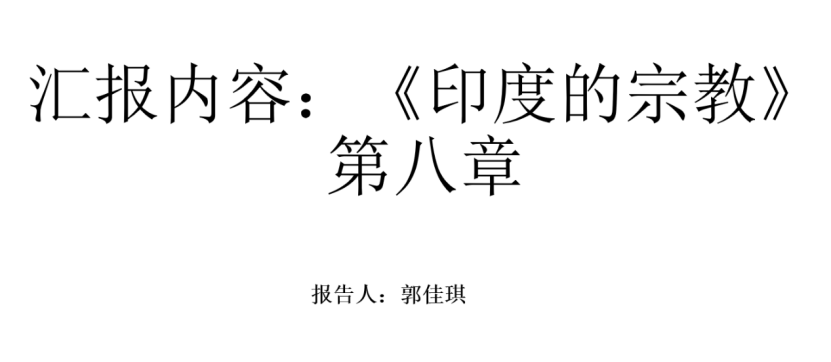
首先,由西北大学硕士生郭佳琪进行汇报,主题是“《印度的宗教》第八章”。他先明确了韦伯做此书的问题意识,是为了研究宗教教义所体现的精神对社会经济和政治的影响,本书核心即印度教的种姓制度是如何阻碍印度现代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郭佳琪具体阐述了社会学中种姓制度的核心概念:先赋地位与自致地位的区别。先赋地位由血缘遗传等先天因素决定,而自治地位则是经过个人的努力而获得的社会身份。印度教认可人的地位显然是先赋的,这种先赋地位自于前世。这就是印度教著名的业报轮回思想,将对低种性者的压迫合理化。四大种姓当中的婆罗门与刹帝利的关系。婆罗门与刹帝利两大统治阶级之间形成了互惠互利的同盟关系。婆罗门从种姓制度的安排中满足了自身的获利动机,在祭祀活动中受到了馈赠,而刹帝利作为世俗统治者则从婆罗门那里获得了统治的神圣性与合法性,确保了其相对于被支配阶级废蛇与首陀螺的支配者地位。著名的研究印度史的学者刘心如认为,在雅利安人内部社会阶层分化的过程中,刹帝利与平民阶级吠舍这两大集团的分化和对立,导致刹帝利与祭祀婆罗门联手,取得政权合法性。
进一步而言,在印度古代社会,早期种姓阶级的分化远非固定,种姓最初仅仅是雅利安人内部的分化。正如韦伯所说,婆罗门种姓最初起源于宗教原始巫师,并逐步转化为主持原始共同体献祭仪式的祭司。随着古代王权与贵族的兴起,其中为王权和贵族提供祭祀服务的家庭祭司压过了共同体献祭仪式的祭司。婆罗门能够在众祭司中之中脱颖而出的原因是其服务的对象身份不俗,婆罗门的祭祀活动构成了雅利安部族之间的文化纽。在雅利安部族的整合过程中,共同祭祀绝工至伟。更是因为共同祭祀,使婆罗门成为横跨雅利安诸多氏族之间的社会阶层。这就解释了出生于巫师从事祭祀活动的婆罗门为什么会凌驾于沙地利种姓之上。但婆罗门远非时时处处控制着刹帝利。韦伯谈到,表面上种姓皆许的决定权操之于婆罗门之手,但“婆罗门从来都不是这个问题的唯一决定者”,“即使在广大领域种姓社会阶级的原有秩序或重新排列,还是操纵在君主手里。”这是因为婆罗门“既非一个较全层级的祭祀团体,也非一个有组织的巫师行会,更不是一个统一的组织实体。”公元前六世纪以摩揭陀国为代表的一大批家产君主制国家崛起,君主凌驾于婆罗门之上的迹象变得开始明显。但婆罗门却抵御住了刹帝利的冲击,韦伯认为原因种姓制度背后的宗教伦理观念在起作用。
而作为四大种姓当中地位最低的首陀罗,它自身内部也存在着分化。这种分类的标准的就是洁净与不洁的观念。这里郭佳琪提到了印度教的形而上学思想。印度教的本体论认为世界的本源或终极存在是被称为“梵”的东西。“梵”分化出所有他者,他者又返回“梵”自身,世界的终极存在是一元的。印度教的这种形而上学思想与德国的绝对唯心论颇为相似。世界万物作为从“梵”分化出的他者,他者与他者之间并非平等的,而是存在着高下之分。这种高下之分是价值性的。体现这种价值性差别的标准,就是印度教的洁净与污秽观念。这种观念使得首陀罗内部被划分成了两大部分:一、地位较低的首陀罗,被婆罗门视为“不洁”的;二、位并不那么低下,被婆罗门视为“洁净”的阶层。
韦伯的分析方法有一种三联体的结构,宗教伦理与政治和经济之间,可以被看作一种分析框架。加拿大学者布鲁斯崔格尔的《理解早期文明》一书中有着类似的分析结构,它的内容是更加具体,有助于我们理解这种三联体结构。崔格尔以(a)社会/政治(b)经济(c)认知与象征这三大部分来比较不同的古文明。这三者形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其框架具有普适性,我们可以将本章中对四大种姓的具体描述归类到这三个部分之下来理解。社会/政治组织处理的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经济,从现代观念来看,是经济/生态,它处理的是人与环境之间的关系;认知与象征或意识形态(观念体系)/宗教,它处理的是人的内省及人的内省之展现。郭佳琪这里为大家展示了崔格尔书中的标题,即他展开分析的对象之分类。(a)社会/政治组织:(1)王权;(2)国家:城邦国家与领土国家;(3)都市化;(4)等级制度与社会流动;(5)家庭组织与性别角色;(6)行政;(7)法律;(8)军队组织。(b)经济:(1)粮食产量;(2)土地所有;(3)贸易与分工专业化;(4)财富的分配。这一方面稍显单薄,自然地理环境等也应被包含进来。例如,印度大部分地处热带,导致原住民肤色较深,遭致外来征服者的歧视;还有印度以农耕为主的生业导致印度人对牛格外重视等等。(c)认知与象征,大致对应于韦伯的宗教伦理:(1)对于超自然的概念;(2)宇宙观与宇宙生成论;(3)祭祀仪式;(4)僧侣、祭典以及超自然的政治;(5)个人与世界的关系;(6)精英的艺术与建筑;(7)识字与专业知识;(8)价值与个人的诉求;(9)文化的常态与变化。
郭佳琪比较了印度教与中国宗教—从“绝地天通”谈起。李零先生认为这个故事要讲的道理是,人类早期的宗教职能本来是由巫觋担任,后来开始有天官和地官的划分:天官,即祝宗卜史一类职官,他们是管通天降神;地官,即司徒、司马、司工一类职官,他们是管士地民人。祝宗卜史一出,则巫道不行,但巫和祝宗卜史曾长期较量,最后是祝宗卜史占了上风。这叫“绝地天通”。在这个故事中,史官的特点是“世叙天地、而别其分主”,它反对的是天地不分、“民神杂糅”。这与印度教的情形是迥然有别的。印度教恰恰没有将宗教与世俗区分开,“民神杂糅”,导致作为宗教巫师的婆罗门竟然凌驾于世俗统治者刹帝利之上。而佛陀在原始佛教传播过程中抬高刹帝利的地位就蕴含着与婆罗门争衡的思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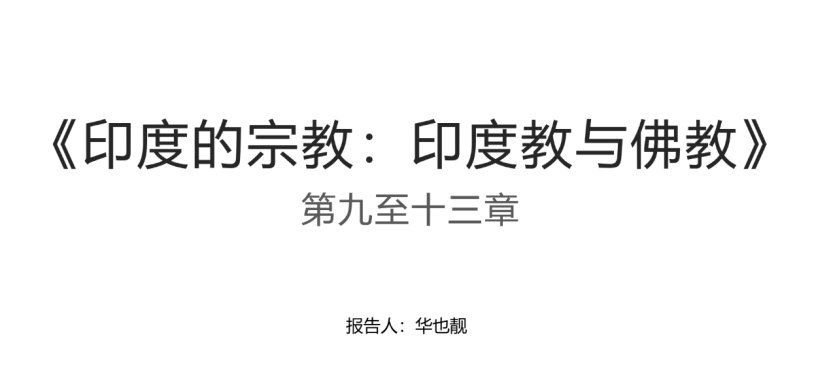
其次,由西北大学硕士生华也靓进行汇报,主题为“读《印度的宗教》第九至十三章”。华也靓介绍韦伯的写作目的,韦伯很关注宗教伦理对于社会的发展,尤其是经济生活的影响。韦伯认为社会的动力是多元的,而非单一元素的。宗教的本质甚至不是我们的关注所在,因为某一特殊的共同体行动类型的条件与效应才是我们研究的旨趣。华也靓展开汇报了九至十三章的具体内容,第九章介绍了种姓的种类与种姓的分裂,以及种姓的分裂形式和分裂的原因。种姓分为部族种姓和职业种姓。部族种姓可以通过名称祖先图腾族内婚形式等等来辨认,而职业种姓相比来说具有排他性。种姓的分裂形式和原因有:以拒绝通婚与同桌共食的形式表现;由于种姓成员的迁徙;部分种姓成员不再遵守某些既有的礼仪规范,或实行新的仪式义务;这是由于1.不承认某些利益规定并采用新规 2.贫富的分化 3.职业的改变 4.部分成员在礼仪传统上的动摇。由于种姓间为礼仪不许的性交或无法调停内部各类纷争手工业种姓的墨守成规:生产部门泾渭分明;种姓成员间不得相互竞争,主顾关系的确保;宗教因素;严格种姓组织:氏族卡理斯玛的世袭制。在缺乏政治统一之处,地区性的种姓分裂现象也就最为显著。在新的种姓与次种性产生原因中,作者最感兴趣的方面是其经济方面的因素以及贫富的分化与职业或技术的变更。第十章,种姓的纪律:种姓处理的问题;种姓的强制手段;种姓的裁决机构(中低级种姓、高级种姓)。纯粹的书记种姓为印度王朝家产制的产物,在此一种姓里,家产体制的历史影响力于今犹存;相异于古来的社会与封建贵族,他们对于高级种姓阶序的要求,远远超平于对身份意识的讲究。第十一章聚焦在种姓与传统主义(经济问题)。种姓秩序,就其整体本质而言,完全是传统主义的,并且在效果上是反理性的。作者还提出了“亚洲民族之停滞性”的原因是种姓秩序整体和整个体系的“精神”。本章节还涉及到韦伯对《1911年普查一般报告书》,得出现象与结论:印度本地人的财富,部分而言相当巨大,长期以来相对地很少投入近代企业作为"资本”;印度教徒的财富很明显地更加倾向于密集的商业投资,印度教的的劳工工作热度是更加强烈的。这两种现象同样都是受到种姓义务之遂行,因印度教而言具有特殊性意义所制约。第十二章内容是关于种姓秩序的宗教救赎意义,涉及印度教教条,唯物论与佛陀作哲学为何被视为异端。其中佛教徒被视为异端的原因是1. 礼仪上不净;2. 佛教徒拒绝承认吠陀与印度教的礼仪有助于解脱,并且自有一套(部分而言)比婆罗门更加严谨的法(Dharma);3.否定“灵魂”的存在,至少否定“自我”这样一个单位的存在。华也靓由此又展开汇报了印度教两个基本宗教原理:灵魂轮回信仰与业报的教义。1.彻底相信任何与伦理相关的行为必然会影响到行为者的命运,并且没有任何的影响会消失掉,此即“业”的教义;2.业报的观念是与个人在社会组织里的命运相结合的,换言之, 相联结于种姓秩序。韦伯对此总结道:想通过经济的理性主义打破传统主义,是根本不可能的。第十三章韦伯提出问题,种姓在印度的历史发展条件是什么,并且具体阐述了印度教种姓制度何以发生于印度。原因有以下几种:1.人种的因素:被轻蔑的被征服者通婚是绝不可能完全得到社会认同的;2.血统权(氏族卡理斯玛)的重要性,朝向固有种姓建构发展:被征服者原则上是一整个再生族的奴仆;手工业通过区域间与种族间的职业专门化来进行(城市及其市场低度发展)并强固;婆罗门将社会秩序予以礼仪性规制,在宗教上定型化既有情势;3.王侯与婆罗门连手共同护卫既有的神圣秩序,凡此皆益形巩固了种姓体制;4.婆罗门特有的神义论。通过对于印度教的研究,不仅可以了解这个婆罗门教义对于人的职业问题的影响,对于种族制制度的构建巩固,还可以深入发掘出,哪些生活样式因此产生出来?而这些生活之道又对于行为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这也是马克思韦伯宗教学研究的重点,也是他所要讨论的问题:就是从宗教行动本身的意义来了解宗教。最后华也靓总结了韦伯的宗教社会学研究的三大主题: (1)重要的宗教观念对普通信徒世俗伦理和经济行为的影响;(2)群体结构对宗教观念的影响;(3)通过对不同文明宗教信仰的原因和结果的比较,来确定西方的特征。
孙国柱老师对两位同学的汇报进行了点评。首先,孙老师对两位同学的汇报表示了肯定,也认可且鼓励了读书会公共汇报的学习方式。孙老师从两位同学做汇报的角度来总结了两位同学的观点以及对我们学习的指导意义:一、从韦伯写作目的的角度出发,“用韦伯理解韦伯”;二、从他人的角度出发,用一些他人的重要研究去帮我们理解韦伯:马克思韦伯就是用一种世界性的、全球性的眼光在解读印度的文化,我们也要通过学习韦伯来理解他人,理解世界,同时善用时空视角的转换去理解世界动态的发展。
孙老师补充说到,印度文明在历史文化角度上的重要价值,并且点出了秩序和自由、秩序与差等的关系,来反思我们的存在,进一步强调了宗教研究的重要意义。孙老师提出问题:什么定义了文明?文明有更加深层的底色。宗教伦理和政治、经济有非常深刻的关系,值得我们去关注和探讨。我们去反思它的时候,对我们在学科上、在文化上,分别有什么启发。韦伯揭示了风俗与秩序的背后,暗含着深刻的文化影响。文化的独立意义,孙老师对文化内核的思考、宗教与文化的关系颇为深刻。他认为宗教是一种天然的调查学科,无论是宗教与社会学,宗教与文化,宗教与人类学,都属于这种广义上的宗教学。鼓励大家对于宗教学的学习,不要局限于单一的形式,宗教学天然就是跨学科、跨文化的专业。也要关注宗教学天然的比较视野,去探寻其背后的文化意义,影响着我们每个人生活的各方各面,影响我们选择的方向、我们认同的程度,也会让我们重新生成价值的判断,形成社会秩序。
孙老师同时也提出了自己的几个关键思考来启发同学们。一、同学们在做汇报时,对于翻译而来的专有名词,可以备注上外文词汇原本的含义,和图文作为辅助;二、可以多思考宗教文化的同异关系,并且更为细致深入的思考;三、印度教发展到佛教,是诞生了新的宗教还是旧有宗教的改革。孙老师给两位同学提出建议:在汇报中关于业报对印度经济到底如何产生影响,这部分缺乏更为细致的探索,在此类比了杨联陞提出了“报”的观点如何对中国社会秩序造成影响,来鼓励两位同学做更深入的思考。孙老师最后总结道:一个完全平等性的社会和是一个完全没有差序的、完全自由开放、流动的社会,和一个相对稳固的社会,我们也不一定能够用先进和落后来区分,人文学科没有标准答案。
随后谢志斌老师提到我们要研读《印度的宗教》的原因。一是西北大学宗教研究和这个历史研究素来有南亚研究的学术传承,以及当下对佛教的研究,都离不开回溯印度宗教;二是印度文明对文化研究来说有其重要地位,但国内研究较少,尤其对于古代文明,古代文化,古代宗教的着力点着力是很少的。这其中研究的价值与意义,需要学者们和我们同学共同努力。谢老师还延伸了孙国柱老师提到的学科建设与东西方文化语境的辩证观点,提醒同学们需要有批判意识,尤其是在面对西方学者来解读东方宗教的现象和本质时。
最后两位同学回应并感谢了孙国柱老师的评议,他的发言帮助大家拓展了理解的角度,指明了学习的方向。
至此,“西北大学玄奘研究院读书会”第95期活动圆满结束。
(编辑:李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