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0月29日晚7点,西北大学玄奘研究院读书会第98期活动在线上举行。本次读书会的主题为“读韦伯《印度的宗教》第二篇一~九章”,领读人为西北大学历史学院在读硕士李佳龙和殷纪泽,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孙海科老师评议。西北大学谢志斌副教授,以及西北大学哲学学院、武汉大学、贵州大学等高校和单位十余名师生在线上一同参与了此次读书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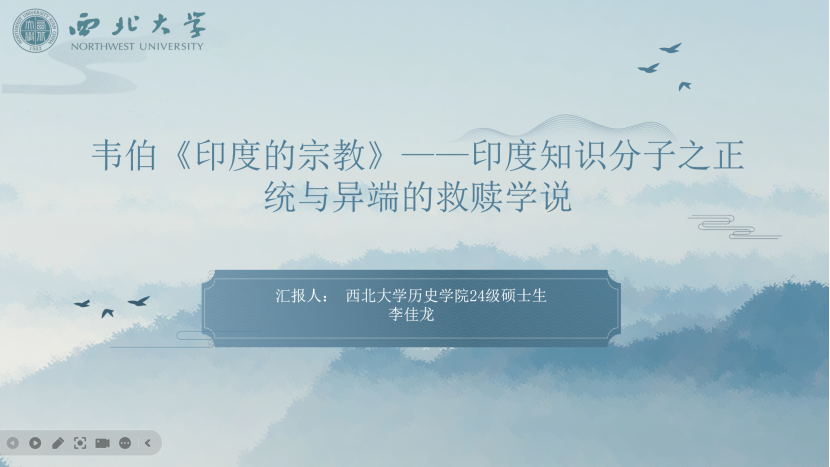
首先,由西北大学历史学院在读硕士李佳龙进行汇报,主题是“韦伯《印度的宗教》——印度知识分子之正统与异端的救赎学说”,他从“婆罗门宗教意识的反狂迷与仪式主义”、“法的概念与自然法的缺乏”、“印度的知识、禁欲与神秘主义”、“沙门与婆罗门的禁欲”、“婆罗门文献与印度学问”五个方面进行展开。
李佳龙同学一开始对韦伯《印度的宗教》第二篇特别是第一到第五章的内容进行了总括性的介绍,指出这一部分韦伯主要是立足于对印度知识分子的宗教思想体系的分析,通过印度宗教体系和西方宗教体系和中国的儒教体系的比较,揭示印度知识分子所具有的某些独特性以及这一群体与印度社会之间的独特关系,例如他们是如何通过宗教、禁欲传统以及法律规范对印度的社会秩序和文化产生影响。
第一章围绕婆罗门宗教意识中的反狂迷与仪式主义展开讨论,并与希腊及儒教知识阶层进行了比较。一方面,婆罗门宗教意识强烈反对狂迷和极端行为。他们认为,只有神圣经典上的知识才是一切福祉的关键,而狂迷和无知是最大的恶。这种反狂迷的态度塑造了婆罗门教养上的骄矜与坚定的信念。在这种反狂迷意识上,李同学将佛教和儒家纳入了比较的视野进行了分析和讨论。另一方面,婆罗门宗教意识重视仪式和祭祀,他们自认为是连接人与神的重要桥梁。而婆罗门阶层以祭献与巫术来保持与王侯的关系,形成了独特的仪式主义性格。仪式主义在婆罗门宗教意识中占有重要地位(祭祀万能——婆罗门教三大纲领之一),甚至影响了印度社会的结构和文化。仪式在这里就被认为富有着神圣力量,超越了任何个体的宗教激情或者狂热。韦伯认为,这种理性化的仪式秩序是赋予了婆罗门教一种稳定性与权威性。也就是说,这就是为什么婆罗门教能在印度诸宗教中具备如此独特的地位。并且韦伯分析婆罗门教的仪式主义的核心特征之一,就是反对狂迷、狂喜、狂热等这样一些非理性因素。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它是对于理性的一种追求。李同学也指出,这里的理性可能与我们平时所理解的的理性概念有一些区别。但是概言之,韦伯认为婆罗门教的仪式主义与许多宗教所追求的神秘体验倾向是有所不同的。从反迷狂到这种仪式主义使得婆罗门的宗教实践相当于一种行为规范,即利用宗教的反狂迷和仪式主义内容去映射到或者说引用到整个社会当中,形成一种社会控制手段,包括强调仪式的一些严格规定。进而使婆罗门教在整个社会当中具有独特的宗教威严,也使得整个婆罗门种姓等级提高。
印度婆罗门与希腊知识阶层的比较就共同点而言,希腊知识阶层和婆罗门都重视知识和智慧,认为它们是解脱和救赎的关键。两者都形成了独特的宗教意识和哲学体系,对各自文明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不同在于,希腊知识阶层更加开放和多元,对宗教和哲学持有一种更为宽容和包容的态度。婆罗门则更加保守和排他,他们坚持认为只有自己的宗教和经典才是真理的源泉。希腊宗教意识中缺乏婆罗门那种强烈的仪式主义特征,而更加注重理性和思辨。而与儒教知识阶层的比较下,二者共同之处是儒教知识阶层和婆罗门都强调社会秩序和道德规范的重要性。两者都形成了独特的宗教或哲学体系,对各自文明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不同之处是儒教知识阶层更加注重人文精神和道德修养,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婆罗门则更加注重宗教仪式和祭祀,认为它们是连接人与神的重要途径。儒教宗教意识中缺乏婆罗门那种强烈的反狂迷特征,而更加注重实用和功利。
在第二章中,李同学总结指出印度的法律体系具有高度的宗教性质。法不仅是一种世俗的行为规范,更是一种宗教义务和生活方式。法的主要来源是宗教经典和传统,主要体现在《摩奴法典》和其他古印度教经典之中。这些经典所设定的法律体系被认为是神圣的,并与个人的宗教修行、生活习惯密切相关。但是,在印度的法律体系中,并不存在类似西方的“自然法”概念。在这里,李同学介绍西方对“自然法”概念的早期理解,认为自然法是一种超越世俗法的、基于理性或道德的普遍法则,强调每个人都享有普遍的、不可剥夺的权利。而印度法体系没有这种普遍性的法律观念。印度的法律关注的是特定社会群体(如种姓)的行为规范,法律的实施和规范具有高度的社会分层性。因此,印度的法律强调社会阶层和个人身份,尤其是种姓制度对法律的影响深远。不同种姓的人在法律地位和义务上存在显著差异,比如婆罗门阶层享有特权,而低种姓则受限于严格的行为规范。这种法律体系并非基于个人的权利和义务,而是基于其在社会结构中的角色和身份。由此可见,古代印度法律较显著的特征有二:其一是与神奇奥秘的宗教教义融为一体,其二是以等级自然的种姓制度为核心。所以,韦伯在这里所强调的是印度的法律体系是一个不太发达的,或者说是缺乏西方所强调具有普遍性的、人人平等的自然法精神的法律体系。
第三章是对印度的知识体系、禁欲传统与神秘主义的讨论和分析。概言之,印度的知识关注的是超越世俗的终极真理,试图通过哲学和宗教追求自我解脱,而非单纯的世俗知识积累。这种以宗教为核心的知识体系,使得学术和智慧在印度具有浓厚的宗教色彩。而禁欲主义在印度文化中占据重要地位。韦伯指出,印度的禁欲思想不仅是一种道德规范,更是通向解脱之道。禁欲的目的是摆脱世俗欲望、达到自我净化,从而接近宗教的至高境界。与此同时,印度的宗教传统中又充满了神秘主义色彩。神秘主义是一种追求与神圣力量直接接触的宗教体验,神秘主义强调个体在神秘体验中获得的主观感受,认为通过这样的体验能够获得与宇宙或神灵的合一。这种神秘体验使得宗教不仅仅是信仰与仪式,而是一种直接的精神感应或“悟道”,这在印度宗教中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
第四章中,转向对婆罗门与沙门这两种同样具有禁欲主义色彩但又承担不同社会角色的比较分析。婆罗门作为传统的祭司阶层,是维持宗教仪式和传统知识的守护者,具有高贵的社会地位和深厚的宗教影响力。而沙门则是一群以修行为主的游离僧侣,他们强调个体的修行与解脱,是印度早期禁欲主义的重要代表。沙门群体不仅包括佛教和耆那教的追随者,也涵盖了其他一些寻求解脱的禁欲修行者。婆罗门的禁欲主义是从其宗教职责和社会责任出发的。婆罗门的禁欲包含了特定的仪式与祭祀规范,这些规范既是对神的虔诚,也是对社会秩序的维护,强调通过履行义务来保持宗教传统的神圣性。婆罗门禁欲的目的是维护种姓制度和宗教等级,并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其社会服务的功能。相较于婆罗门的禁欲,沙门的禁欲更强调个体的精神超越与解脱。沙门群体认为,世俗生活是苦难的根源,必须通过严苛的修行如冥想、斋戒和放弃财产等手段,彻底摆脱对物质生活的依附。沙门的禁欲方式追求的是对内在世界的探寻和精神的净化,具有较为激进和自我超脱的特点,力图通过放弃世俗成就个人解脱。他们的禁欲主义往往在社会结构之外,带有反传统和反世俗的色彩。
第五章集中对婆罗门文献与印度学问体系的讨论。婆罗门经典文献最早期的是《吠陀经》,它们主要是宗教颂歌和祭祀仪式的记录,反映了早期婆罗门教的信仰和仪式。后来的《奥义书》则在哲学和形而上学上具有重要地位,探讨了宇宙本质、自我与解脱等深刻的哲学问题。此外,《摩奴法典》等文献则侧重法律和社会规范,为社会秩序提供了框架。通过这些文献,婆罗门阶层掌握了宗教和知识上的主导权。以婆罗门知识体系为主的印度学问与世俗的科学或学术知识不同,婆罗门的知识主要服务于宗教目的,强调与神圣的沟通和对超自然的理解。这种知识体系不追求实用性或创新,而是致力于解释和维持既有的宗教信仰和社会秩序。因此,印度的知识学问发展始终围绕宗教核心,缺乏独立的科学或理性探索。
李佳龙同学最后分享了一些国内相关的学术研究成果,例如婆罗门教与中国儒家的比较研究、印度法的内涵研究、印度禁欲主义研究、对韦伯宗教观的研究等。

接下来,是西北大学历史学院在读硕士殷纪泽进行汇报,主题是“《印度的宗教》六到九章——救赎的手段、目标与方法”。他首先介绍了一下自己在这四章的阅读方法,即采用文本分析、原典参照和成果借鉴三种方法的结合。他认为,韦伯文本内容在总体分析性的笔调中不乏晦涩、抽象的表达,这需要读者仔细审视其中关键词句的含义和语境从而推断出作者时而隐晦的原意。在理解文本的基础上,他将文本内容用论题论点的形式分条陈述,从逻辑上进行了比较清晰的梳理。这四章的内容多涉及到印度传统思想和宗派,这些思想都能够在吠陀经典系统中找到根据,因而他也将部分重要思想背后的原典内容加以附录。同时,为了更好地理解印度传统宗派补充了一些相关学术研究成果。
然后殷纪泽同学对六到九章进行了一个概述。他认为这四章的内容围绕着中心词“救赎”展开。这里的救赎,是从印度传统宗教思想中的意涵来说,即是指个体灵魂摆脱在无常世界经验到的痛苦从而获得解脱的过程。从一定意义上讲,所有印度的宗教思想都是以救赎为中心问题而展开,然而随着历史的发展不同宗派之间对于救赎的目标、方法与准则产生了不同的思考和实践。这四章文本内容分别从瑜伽行者、正统六派、薄迦梵派、异端教派四种宗派的视角对于救赎理论的哲学思辨和修行实践进行了系统性的阐释和对照。通过深入剖析和详细对比上述印度教派的救赎理论,我们可以系统梳理印度传统宗教对于灵魂本体和世界本原的哲学构建以及瑜伽技术和苦行冥思的修行实践。特别地,韦伯注重将教派之间的义理诤论和教派所传播的阶级之间的矛盾所结合起来分析,深刻呈现了社会阶级基础和宗教上层建筑之间的辩证关系。在进入正式的文本内容前,殷同学参考孙晶老师的《印度六派哲学》和《印度吠檀多不二论哲学》进行了一些基础介绍。印度经典系统主要分为了吠陀系统和史诗系统,他首先对“四大吠陀”的主要内容进行了介绍,其次是对印度数论派、吠檀多、瑜伽派、胜论派、弥曼差派、正理派等六大传统宗派的特征归纳。
在对文本的正式领读中,殷纪泽同学首先指出,第六章《救赎技术(瑜伽)与宗教哲学的发展》主要由两部分组成:瑜伽术的基本构成和瑜伽术的神秘主义与婆罗门的主智主义。在瑜伽术的基本构成中主要是分为三个部分,即瑜伽术的调身技巧、瑜伽术的调息技巧、瑜伽术的调心技巧。而韦伯的分析指出,瑜伽行者是不被传统婆罗门阶层接纳的一个独立的修行团体。并且,瑜伽行者注重通过非理性的修行经验获得救赎,传统婆罗门更看重可以理性论证的知识。婆罗门出于对灵知的追求并不排斥瑜伽的方法,两者在一定程度上紧密结合。
在这里,殷同学还详细介绍了瑜伽派宗教哲学及实践瑜伽修行的方法主要分为场所的选定、坐法、呼吸的调制、五官的抑制等渐进次序,最后至意念的集中。印度人对场所的选定主要是在寂静的林间等地,坐法包括半跏趺坐、结跏趺坐等。呼吸的调制是去除妄念、心气镇静等,如不这样则不能进而进行五官抑制以达到意念集中。当然,瑜伽修行并非易事,要实行修炼必须要严格按照瑜伽修行的诸种规定来执行。首先按外修法,然后再实行内修法;外修法修的是身体,又称“行瑜伽”;内修法修的是道德、精神以及与身体的综合修炼,尤其重视禅思的活动,故又称“智瑜伽”。它们一共分为八个阶段,或称八支行法,即夜摩、尼夜摩、坐法、调息、制感、执持、静虑、等持等。而瑜伽派与其他宗派的关系上,瑜伽哲学也是六派哲学中最缺乏独立性的一派,因为其他五派都有自己独特的哲学理论,而瑜伽哲学的行法却又是印度自奥义书以来所有的哲学派别都通用的修行法。接下来也对瑜伽的历史起源、瑜伽的吠陀解释、瑜伽的发展历程进行了简要介绍。最后对瑜伽派的哲学思想进行了简要讲述。《瑜伽经》认为,心的本质是同样的,但它的属性却各有异。心的属性主要是三德,心体是由细身组成;它与神我结合,无论过去或未来都常住。心的作用是根据三德的变化而发挥作用的。但有显性作用和隐性作用之分。根据《瑜伽经》,心的作用是前世熏习的结果,也即今世的经验是未来心作用的种子。因此,要想限制心作用的活动并非只要让神我独存就可以,这就是为什么认为让心作用灭除的瑜伽有存在的必要性。瑜伽用磁石和铁的比喻来说明心物的关系。物只要接近于心,心的作用就会显现出来;认识作用就会产生。因此,心的作用归属于能观的神我,能观是不会发生任何变化的;对于能观来说,心也可以作为一个所观,它自身是不发光的。一个心它不可能同时既是能观又是所观,心其实是纯粹能观和现象界之间的媒介,接受能所两观的影响,一切的对象都为能观所认识。对能所二观进行区别时,只要灭除对我的执着,便可以获得最终的解脱。
在第七章《正统的救赎理论》的领读中,殷同学首先解释了所谓“正统”就是指此前提及的六派哲学的救赎理论,印度流派哲学共同继承自吠陀经典,因此被称为“正统”。然后婆罗门教的冥思技术主要在三点呈现:虔诚地凝神于古老圣音“Aum”;从日常生活中解脱出来,准备进入一种究竟的境界;提倡和缓的节奏,也不鄙弃激烈的苦行主义。其次,婆罗门教对基督教神圣空间的拒绝是一
个值得关注的点,基督教经典中描绘的永恒的天国至福不会被婆罗门教视为修行目标,而且以人类有限的功德,从业报轮回的原理上不可能永处天国,因此追求在此世中解脱而达到涅槃的境界,胜过去彼岸世界的动力。从上所述,婆罗门教认为世界的无常性是烦恼的来源,无常性普遍附着于一切凭感官知觉得到或是凭想象力得到的对象,.世界的本质是个体灵魂在永恒秩序的主宰下不断体验轮回的过程,而“救赎”就是指灵魂从永恒秩序的主宰下解脱并获得绝对的自由。在这里韦伯对《富兰那书》中神话叙事的三段论进行了考察:在卡利时代,梵睡着了,因而首陀罗与异端抬头使得世界走向混乱;随后,毗湿奴以湿婆之形现身,以可怕的毁灭力量破坏了世间;最后,梵以赐福神的形象苏醒过来,使得世界重新建立。同时,梵天也具有三重神性:作为施咒术者所祈祷的对象具有巫术性特征;作为世界产生的源头具有创世性;作为超出一般功能神与地方神的至高神性力量具有超神性。总体来说,正统派教义中救赎的实现方式以个人主义为立场,相信个人最终优先为自己获救而修行,相信灵魂轮回与因果报应对个人命运的主导作用,并重视个体灵魂构造的形而上学理论。而在正统教义中,转世轮回具有一种本原力量。如《穆达卡奥义书》认为呼吸是人体中非物质的、心灵的、精神的实体,推动着人的轮回;《旃多格耶奥义书》认为一种精神性自我的灵体伴随呼吸而成型并推动着轮回作用;《美特罗耶那奥义书》认为思维成为轮回转世的根本动因。而《奥义书》中所描述的灵魂运动的本原力量类似中国道家的阴阳二元论,奥义书将灵魂运动的根本力量分为男性的神我与女性的自性。不过,灵魂的三德是纯质、激质与翳质,这三种力量从光明与黑暗的两个方向推动着灵魂在轮回中的运动,神我并不直接参与到世界的任何活动中,反而可以认为是作为观察者存在。由此而来正统派对于伦理的规范就体现为《律法书》中主张的八种基本德行:慈悲、忍耐、不嫉妒、纯洁、平静、正生、不渴求、不贪婪。在《摩奴法典》中转变为较积极的十种品质:寡欲、忍耐、自制、不偷盗、纯洁、制欲、虔敬、知识、诚实、不动怒。八德或十德的伦理规范具体也可以浓缩成五戒:勿杀生、勿妄语、勿非梵行、勿偷盗、勿嗔恨。此外,关于传统婆罗门与推崇《奥义书》的革新派的分歧之处,传统婆罗门将礼仪视为至高无上的规定,如《家庭书》和《律法书》中所述,是直接影响着灵魂善恶轮回的根本性规定。推崇《奥义书》的灵知主义者倾向于赋予传统礼仪新的诠释,将礼仪视为灵知主义理论大框架中一个有机成分从而弱化其功效。而沙门是否需要符合律法书上的传统礼仪是两派诤论的焦点。守旧派认为沙门应当像律法书上所写经历成为家长并生养子嗣的过程,革新派认为有志于苦行的沙门可以跳过这一世俗过程。此外,灵知主义者认为灵知为最高的救赎手段。灵知是超脱无常世界(包括人间与神界)的最高救赎手段。然而,对于灵知的理解可分为两个大相径庭的派别。灵知现实论认为,灵知是对现实的物质-灵魂-精神过程的认识,决定无实体的本我与有实体的世界之间的交互关系。灵知超越论认为,灵知是对现实世界虚幻性的体察,并由这种体察得到了对于世界无常本质的认识与解脱。
综上所述,公认的正统性学派可分为六家:数论派、吠檀多、瑜伽派、胜论派、弥曼差、尼夜耶,六大学派的正统性来自于对吠陀经典的继承。正统学派承认三种救赎方法:礼仪行事、禁欲苦行、灵知,并认为灵知是获得解脱的最高手段。灵知的全然掌握具有两重验证标准:第一,当下享有禅悦。第二,此世解脱业报。
在《薄伽梵歌》的救赎论与职业伦理中,殷同学指出,韦伯认为《薄伽梵歌》解决骑士阶层的救赎需求:骑士阶层无法像婆罗门阶层一样通过礼仪和冥思实现救赎,只能从现实的义务层面出发寻求解脱之道。为了解决骑士阶层的救赎问题,正统六派的救赎论发生进一步转变,异端宗教的救赎论也随之产生。《薄伽梵歌》的内容包含了正统宗派关于剎帝利阶层救赎问题的探讨,在哲学上具有很强的延展性。而《薄伽梵歌》中形成了国王和骑士的天命观。骑士阶层从气质上不倾向于传统婆罗门那样进行业报轮回的哲学思辨,而是倾向于较为感性的至高神崇拜和天命信仰。《薄伽梵歌》描绘了克里希纳作为最高神的存在,并通过最高神的教导使得骑士找到了战争的合义理性。《薄伽梵歌》所宣说的教理使得骑士不得不进行战争的律法约束和追求解脱的救赎渴望得以协调。而实际上,《薄伽梵歌》对于吠檀多派幻化理论进行了宣扬。《薄伽梵歌》中克里希那教导有修不必为幻化的战斗而感到背负恶业,这是运用吠檀多派的幻化理论使得骑士免于现实行为的困扰。进一步而言,《薄伽梵歌》教导人们无欲而行,即在履行现实义务的同时又得以从现实因果中解脱。《薄伽梵歌》的现实解脱论为剎帝利阶层的伦理提供很好的救赎依据,然而却与传统的业报决定论形成分歧。而另一方面又与瑜伽行派具有亲密关系。从解脱观上看,薄迦梵信仰与瑜伽行派都追求以当下解脱为最高境界。从戒律规范上看,薄迦梵信仰提倡位于极端苦行和享乐主义之间的中道原则,这与瑜伽行派高度相似。从修持方法上看,薄迦梵信仰和瑜伽行派都主张通过“Aum”字音的念诵与宇宙合而为一。但无论如何,薄迦梵信仰是对于至上神克里希那的皈依。薄迦梵信仰将至上神信仰置于其他信仰之上,并认为皈依至上神是根本救赎之道,至上神的权能之大甚至于可以使人免去恶业的罪罚,获得至上神保佑能够使得现实生活中律法所规定的义务转化为得到蒙恩的福报。在此之中,《薄伽梵歌》中就包含着各个阶层的不同视角:骑士阶层既为自身剎帝利武士的身份感到光荣,又畏惧因战争杀戮所带来的罪业;市民阶层渴望自身能够在日常律法的规范框架中获得至高神的救赎;祭司阶层出于对宇宙本体和个人精神的深刻认知从而对现实生活感到淡漠。因此,薄迦梵派特别重视救赎确证。薄迦梵派认为个人的灵性资质高下不同,认为那些具有高灵性的人应当尽可能按照瑜伽的方式行为并追求灵知。对于高灵性的人而言,光是通过持戒苦行或是吠陀知识不足以达到与至高神合一的境界,还需要得到最高神恒常不变的加持。临终之人时刻忆念至高神克里希那便容易得到最高神的加持。总的来说,《薄伽梵歌》的教义深刻影响印度伦理的形成。印度人秉持一种宽容的伦理,即不是死板地通过一成不变的宗教标准要求所有人,而是通过有机地将伦理标准划分为不同层次进行灵活地要求。划分伦理的标准除了种姓制度外,还取决于个人的修行目标。而认为各个领域的固有法则和伦理在得到至高神救赎的最高伦理之前会产生一定程度的贬值。限于时间关系,在第九章《上层职业僧侣的异端救世论》中,殷同学直接通过文本本身对耆那教的一些相关内容进行了分享。
孙海科老师对两位同学的汇报进行了点评。
孙老师认为两位同学结合近些年的一些研究成果拓展了大家的视野,并指出韦伯的这本书出版比较早,一些观点受时代局限,现在我们看来可能是值得商榷的,所以我们还要结合着比较新的一些研究成果来进行全面的把握。孙老师结合自己的感受与我们分享了他对韦伯这些观点的一个整体理解和部分比较细节观点的看法。
首先,在阅读包括且不限于韦伯等前人著作时,都要保持一个怀疑的态度,也就是平常所说的“不能尽信书”,尤其是离我们时代有一定距离的一些作品。
第二点是“流动的假名”,具体来说就是无论是谈论印度宗教,还是谈论印度宗教中的某个派别时,我们处理的对象都是流动而不固定的,它们都是在时间序列中不断发展变化的。因此谈论一个学派,乃至一个思想体系的时候,譬如谈论佛教的“无我”思想,它们都不是“常”的,而是“无常”的,是在随着时间的流变而不断迁变的。所以,就需要我们去把握深藏其中的思想史脉络,把他们放到时间中考察其演变。比如韦伯对印度宗教的考察是有缺失的。此前所说的有些描述和总结可能是比较早期的印度婆罗门教的一些特点,但有些则是相对晚出的。比如六派哲学,还有更晚的以商羯罗为代表的相对革新的印度教,可以说从商羯罗变革之后,婆罗门教走向了印度教。在这里,时间的跨度是拉长的,那么在这个拉长的过程中就更需要把握其中的思想史脉络,但是韦伯可能没有特别注重从这样一个脉络上去把握它,更倾向于一个总体性描绘。那么这个总体描绘就可能相应产生一些问题,比如过于宏大而在细节方面存在过失。
此外,韦伯有自己的一个文化立场,始终是建立在西方文化的立场上进行的。韦伯的另外一本著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体现出他一直试图在宗教里面去发现现代人和现代社会法则背后历史所埋下的“伏笔”。他在探讨印度宗教时,我们依然可以看到这种尝试,即印度宗教的背后所蕴含的能够符合现代社会的伦理或者法律精神是什么?或者说有没有?那么这里存在的问题是,作者在写作过程中不自觉的,现在可以称之为“西方中心论”的立场,这个问题是需要反思的。例如前面同学讲述内容提到的“救赎”一词。一方面,这里有某种翻译的问题,但另一方面“救赎”一词本身就是具有较为明显的西方希伯来宗教色彩的词汇。而在印度宗教,也包括更广大的东方宗教中,救赎的观念可能并不强烈。救赎相对应的“罪的观念”在婆罗门教、佛教这些印度宗教,以及中国的儒家等等,本身也不强烈、不明显。所以,救赎一词用于印度宗教分析是值得商榷的。而从印度自身出发是有更合适恰当的词的,即解脱。
另一方面是一些细节问题。韦伯对印度宗教和儒教的比较不够深入,也并不全面。譬如在仪式上,他认为这个婆罗门教更加注重仪式和祭祀,但这里就忽略了,中国的儒家或者甚至称之为儒教,它是有自己比较发达的仪式和祭祀系统的。并且这些在儒家文化中也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一系列的礼仪文化和相应的经典,还有对天、地、神灵乃至地方神的祭祀都有非常完备的体系。此外,韦伯认为其褒扬的希腊宗教所呈现的理性和思辨,在婆罗门教中没有表现出来。但婆罗门教本身就是一个流变的宗教。在婆罗门教早期,可能确实不够发达,但进入到森林书和奥义书时代,尤其奥义书的时代,思辨和哲学已经比较发达了。相应的,希腊的宗教中也没有韦伯所认为的如此发达的理性和思辨,而且他所指的希腊宗教,是否已经直接将古希腊哲学纳入其中。另一方面,韦伯谈论印度宗教时是否真的直击要害是可以反思的,例如他婆罗门教特点的概括,禁欲主义、神秘主义这些是否在印度文化的整体体系中真的如此重要乃至具有核心地位。
最后,孙老师鼓励大家阅读要形成自己的观点,也要借鉴其他人的研究成果,尤其是新近的一些研究成果。在研究某个宗教或某个国家的文化时,一个很重要的阅读来源是这个国家本土人的看法。例如考察古印度的宗教文化,一定要去把印度人自己如何看待、怎么认同他们自己文化纳入视野,寻找他们本国作品阅读,对比局外者对印度文化的描述和本国人对印度文化的描述的差异。譬如我们研究中国哲学、中国文化,中国人写的书和美国人或者德国人写的书是有差异的,无论是关注点还是叙述方式都有不同。所以我们一定要扩大阅读面,从更加全面的角度去把握一个文化体系、宗教体系或者知识体系。
最后,两位同学回应并感谢了孙海科老师的评议,他的发言帮助大家更全面地理解了韦伯的观点,也勉励大家要进行批判性阅读、带着问题阅读,由此指明了阅读和学习的方向。
至此,“西北大学玄奘研究院读书会”第98期活动圆满结束。
(编辑:李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