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1月5日晚七点,西北大学玄奘研究院读书会第99期活动在线上举行。本次读书会的主题为:“古文献研读——《出三藏记集》第7堂 竺法护传”,领读者为西北大学硕士生沈奥。西北大学李永斌副教授、上海大学人文学院黄凯老师,西北大学历史学院以及山东大学、贵州大学、苏州大学、西北师范大学等高校的十余名师生在线上一同参与了此次读书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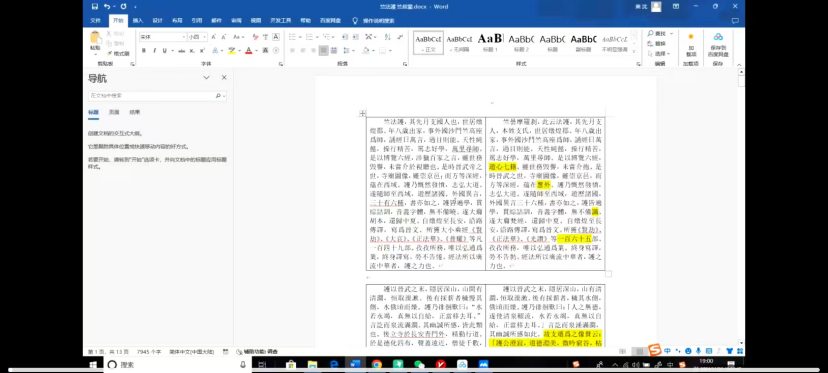
《竺法护传》第一部分的内容由西北大学硕士生沈奥同学为大家领读,他将《出三藏记集》与《高僧传》中关于竺法护的记载进行对勘阅读,他的介绍分为四个部分,分别是竺法护生平研究的相关成果介绍、竺法护的译经活动的相关问题讨论、对文本“后立寺于长安青门外”的考证与原典精读。
首先,沈奥介绍了竺法护生平研究的相关成果。第一,他引入〔日〕境野黄洋《支那仏教精史》(东京:境野黄洋博士遗稿刊行会,1935年,第163—207页)、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128—133页)、李尚全《竺法护传略》(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11年)等文献的研究,对竺法护的生平事迹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概述;第二,沈奥对竺法护籍贯研究成果进行了综述介绍,斟酌辨析了林梅村、荣新江、平井宥庆、王惠民等学者的观点,最后参考了林梅村教授在《贵霜大月氏人流寓中国考》(收入作者《西域文明——考古、民族、语言和宗教新论》,北京:东方出版社,1995年,第47—48页)一文,结合“其先月支国人也,世居敦煌郡”的原典记载,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即,竺法护是世居敦煌的来自大月氏的胡人;第三,借助马德《“敦煌菩萨”竺法护遗迹觅踪——兼论莫高窟创建的历史渊源》(《佛学研究》2017年第1期)的研究,总结出竺法护生卒的时间范围,即,竺法护为230年前后出生,310年前后去世;第四,对现代学界以曹仕邦、Antonello Palumbo(白安敦)、梁富国与姜虎愚等为主要代表的学者关于竺法护生平其他方面研究成果进行了介绍。(参见:曹仕邦:《竺法护引导经法广流中华的民族背景》,《南洋佛教》第198号,1985年,第5—7页;《竺法护引导佛法“广流中华”的民族背景》,《大陆杂志》72卷1号,1986年,第26—28页。Antonello Palumbo(白安敦), “ Dharmaraksa and Kanthaka: White Horse Monasteries in Early Medieval China,” G. Verardi and S. Vita, eds., Buddhist Asia 1: Papers from the First Conference of Buddhist Studies Held in Naples in May 2001, Kyoto: Italian School of East Asian Studies, 2003, pp. 167-216.梁富国:《竺法护与鸠摩罗什入华传教比较研究》,硕士学位论文,西北大学,2008年。姜虎愚:《从洛阳向太行——多元视角下西晋十六国北方佛教研究》,博士学位论文,武汉大学,2020年。)
其次,沈奥同学以文章中“所获大小乘经《贤劫》、《大哀》、《正法华》、《普耀》等凡一百四十九部”为切入点,借助Mai Lai Man(梅迺文)、Daniel Boucher(包达理)和河野訓等三位学者的博士论文,讨论了竺法护的译经活动的相关问题。其中,梅迺文认为竺法护所译的经典,从始至终都受到了中亚佛教思想的影响(Mai Lai Man, Dharmarakṣa and His Work: The Impact of Central Asian Buddhist Thought in Translating Buddhist Texts in the Third to Fourth Century China,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 1994.);包达理则着重讨论了竺法护译本中与梵文不一致的地方,提出了竺法护译经所据的胡本应以佉卢文字的犍陀罗语写本为主的观点,同时他也强调竺法护对文本的改造是为了迎合中国的读者,促进了早期佛教的中国化(Daniel Boucher, Buddhist Translation Procedures in Third-century China:A Study of Dharmarakṣa and His Translation Idiom,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1996.);河野训利用正史和佛教文献讨论了竺法护的生平时代,以及社会环境因素对竺法护个人及译经活动的影响,继而梳理竺法护的译经数量以及每部佛经的翻译年份,并突出竺法护从不熟悉汉语到约四十年后的译经用语变化。并以《正法华经》《渐备经》《如来兴显经》三部典型的竺法护译经为例,讨论了竺法护译经的方法、用语、风格特征等因素。(河野訓:《初期漢訳仏典の研究:竺法護を中心として》,伊势:皇学馆大学出版部,2006年。)此外,沈奥同学参考境野黄洋、葛维钧、辛嶋静志、河野训、真野龙海法国汉学家罗禅能(Jean-Noël Robert)、白景皓、李小荣、真野龙海与萧世友的最新研究成果,对于《正法华经》的翻译研究情况进行了全面而细致的梳理,着重介绍了辛嶋静志在《汉译〈法华经〉的文本研究——基于梵文和藏文版本》一文中提出的观点,即《正法华经》的原语是用佉卢文字书写的犍陀罗语或犍陀罗语和梵语混合的语言。萧世友在《正法华经》的翻译中指出,两晋十六国时期的翻译模式展示了更加系统和复杂的组织,精通中文和梵文的翻译人员的加入,以及对校对的日益重视,标志着以团队为基础的经文翻译史上的重要进步,为以后的译经活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时,其他竺法护译经的研究也引起了学者的关注,例如〔日〕岡部和雄、段晴与Stefano Zacchetti(左冠明)等三位学者,分别讨论了《贤劫经》在古代于阗的传布及竺法护的译经风格、《光讚般若经》的翻译风格等问题。
再次,对文本“后立寺于长安青门外”进行详细的考证,引入西北大学学者杨绳信对敦煌寺的地理位置和历史沿革讨论,介绍了其“汉城之“青门”为宣平门,敦煌寺为曹魏末年时建造的寺院”的观点(杨绳信:《竺法护与敦煌寺》,柏明主编:《宗教研究论集》,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57—367页;杨绳信:《汉城青门考》,《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3期,第94页);几乎与杨绳信同一时间,西北大学李利安也开始关注敦煌寺。李利安对敦煌寺进行了实地考察,对敦煌寺的位置、起源、演变进行了考证,系统性研究敦煌寺的论文,解决了敦煌寺建造者和建造年段的问题。确定了敦煌寺的准确位置是在汉长安城东北部青门的外侧;并结合文献记载,判断白马寺与敦煌寺并非一寺,谨慎地把敦煌寺建寺时间定于公元286年之前(李利安:《中国最早大规模翻译佛经的场所:敦煌寺考》,《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1期)。
最后,沈奥同学带领大家回归原典,详细说明了原文中许多重要之处的注释。第一,文本中“外国异言,三十有六种”中的三十六参考中国史研究论文,认为这一数字实是受到秦汉以来的谶纬影响的具有神圣意义的虚数;第二,《出三藏记集》与《高僧传》文本中列举的竺法护译经著作存在着差异,《出三藏记集》有《大哀》而无《光赞》,《高僧传》中有《光赞》而无《普耀》、《大哀》;同时,《出三藏记集》记载译经总量为一百四十九部,《高僧传》竟高达一百六十五部。沈奥同学指出,两书译经方面内容的异同比较可以参阅河野训和包达礼的论文进行深入的考察;第三,《高僧传》的记载比《出三藏记集》中多了“故支遁爲之像賛云:’护公澄寂,道德渊美,微吟穷谷,枯泉潄水。邈矣护公,天挺弘懿,濯足流沙,领拔玄致。’”和“护既道被关中,且资财殷富”的内容。沈奥同学指出,竺法护的财富主要源自敦煌居士的慷慨布施,同时,他通过吸纳本地大族加入佛教的方式传教,这些大族皈依后也成为了他资金的重要来源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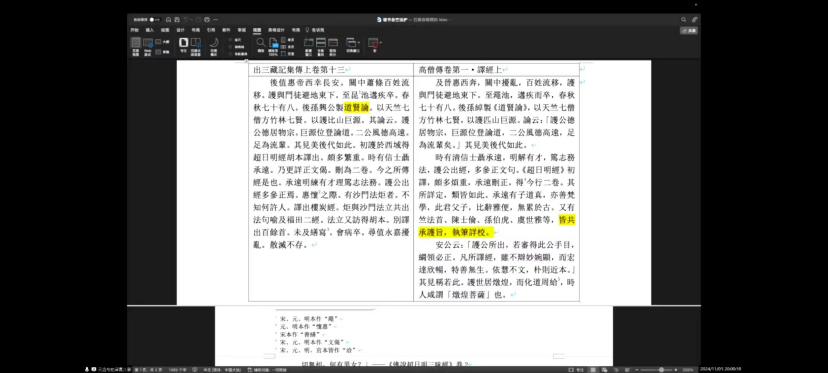
《竺法护传》第二部分由西北大学硕士生吴远兮同学进行汇报。首先,他同样地将《出三藏记集上卷第十三》与《高僧传》卷一《译经上》的第一段内容进行了比较阅读,详细说明了原文中多处注释。首先,《出三藏记集》文本中“至昆池遘疾卒。”中的“昆池”本校宋、元、明本与对校《高僧传》卷一《译经上》应作渑池。其次,吴远兮同学指出《道贤论》文本中将西晋至东晋初年之高僧竺法护、竺法乘、于法兰、于道邃、帛法祖、竺道潜、支遁等七人,依次比为山涛、王戎、阮籍、阮咸、嵇康、刘伶、向秀等竹林七贤的论述体现出了以《道贤论》作者孙绰为代表的江南知识分子从玄学视角展开了对佛教探求。此外,吴远兮同学对《道贤论》的文本进行了拓展阐述,他指出,正始玄学所蕴含的老庄哲学思考,尤其是《世说新语》一书对于当时译经文本的建构,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影响。随后,吴远兮同学指出,根据《出三藏记集》与《高僧传》中的相关记载,我们可以清晰地认识到以聂承远为代表的竺法护译经团队成员不仅是佛经的记录者与书写者,而且对竺法护所的翻译佛经的内容进行了参酌校正,沈奥同学进一步指出《高僧传》比《出三藏记集》的记载多出了“《超日明经》初译,颇多烦重,承远删正,得今行二卷。其所详定,类皆如此。承远有子道真,亦善梵学,此君父子,比辞雅便,无累于古。又有竺法首、陈士伦、孙伯虎、虞世雅等,皆共承护旨,执笔详校。”的说法。这体现出三个层面的重要信息:第一,竺法护时期,民间译经已经达到了相当大的规模;第二,当时竺法护的译经团队已经对佛教义理有了较为深入的理解;第三,竺法护译经团队对于汉语的应用译经达到了文理兼美、文质彬彬的境界。
然后,吴远兮同学又结合文献资料为我们补充了关于两项关于当时佛教情况的重要研究成果。第一,《道贤论》为我们提供了理解佛玄关系的全新视域。汤君教授在《“天竺七僧”、“竹林七贤”与东晋文风》一文中提出,“《道贤论》是中国知识分子尝试理解佛教理论而做出的尝试,它代表着中国学者对佛教思想的接受。”在《道贤论》中“夫佛也者体道者也。道也者导物者也”这样的表述体现出在玄学思想家认为佛教是对“道”的延展,佛道的关系实则殊途同归,从最为根本的逻辑层面上已然接受了佛教;而“周孔即佛佛即周孔”的论述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直接联系儒家与佛家的宣言。吴远兮同学解释道,《道贤论》体现出作者认为很多后世的儒生在理解孔子思想时,往往将其思想学说固化了,实则不应该将儒家学说过度地窄化、教条化的态度,而应该将佛教思想与圣人之言互相融合起来。第二,吴远兮同学参考周玉茹教授《竺法护的佛经翻译与汉地女性佛教信仰的发展》中的研究,探讨了《佛说超日明三昧经》文本体现出女性观念的发展情况。《佛说超日明三昧经》里有着诸多相关表述,像“本无所有,从心所行,各自得之。至于本无,无幻无化、无合无散亦无处所,乃成佛耳!”以及“一切无相,何有男女?”等内容。这些论述实则展开了关于男女的性别在成佛难度上是否存在差别的探讨。《佛说超日明三昧经》明确指出,成佛的境界并不能依据一个人的身份来判定其达成的可能性,众生皆具备成佛的可能,而众生成佛这一点正是众生平等所应涵盖的要义。竺法护将这样的思想引入中国,为后世女性僧团的发展开启了先声,奠定了一定的思想基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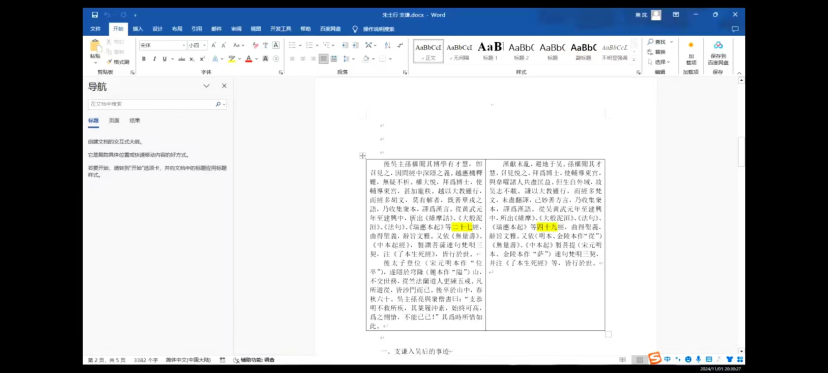
《朱士行、支谦传》第三段的内容继续由沈奥同学为大家领读。他细心地将《出三藏记集》与《高僧传》的文本内容进行了对照阅读,精心挑选出其中的关键章节与重要语句,并借助丰富的学术文献资源,对这些内容进行了深入而详尽的阐释与解读。
首先,从入吴时间、辅导东宫为谁和卒年推断三个方面对支谦入吴后的事迹进行考察。第一,《出三藏记集》载录,支谦抵达吴国的时间为“献帝之末”,而《高僧传》则记述其入吴是在“汉献末乱”之时,两者均未提供确切的日期信息。在此基础上,当代学者邓攀在其发表于《南京晓庄学院学报》2008年第4期的论文《支谦生平略考》中,巧妙地依据《三国志》卷四十七《吴书·吴主传》的相关记载:“(建安二十五年)秋季,魏国将领梅敷派遣张俭前来请求归降并接受安抚,同时,南阳郡的阴、酂、筑阳、山都、中庐五县共有五千户民众也归附了吴国。”的历史背景,提出了支谦可能于建安二十五年冬季进入吴国的推断。沈奥认为这确实不失为一种合理的见解。第二,关于“东宫”所指的具体人物,存在孙登与孙和两种不同解释。汤用彤在其著作《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第107—108页)中提出:“支谦是否曾辅导东宫,尚难确定,且时间亦不详。但若此事属实,那么所谓的东宫,很可能是指太子孙登。”然而,学者邓攀在引入刘雅君关于太子中庶子的研究成果后,提出了不同的看法:“根据‘与韦曜诸人共尽匡益’的记述,可以推测这里的太子应为孙和。”针对这两位学者的观点,沈奥同学进行了细致的辨析,并对邓攀的推断表达了疑虑。他指出,曹魏取代汉朝与孙和被立为太子之间相隔了二十余年,因此,支谦完全有可能在孙登担任太子期间担任东宫的辅导工作。第三,关于支谦的卒年推断,学界存在不同观点。学者邓攀认为,支谦的去世时间应位于建兴二年至太平三年之间,以公元纪年大致可对应为253年至258年。他进一步推测,支谦停止译经的建兴二年或许正是他的卒年,因为在那之后,支谦可以更专注于佛教事业,而译经活动的中断很可能是由于他生命的终结。然而,王毓在《支谦传》(凤凰出版社,2017年版,第24—25页)一文中则提出了另一种看法,即支谦去世的时间最有可能是在孙亮心志逐渐成熟,但尚未亲政,却已有雅兴和能力去关注幽微思想世界的时期,即孙亮十二三岁左右,这大致对应于公元255年前后。
其次,对于支谦译经的数量,学界进行了深入的考证。根据《出三藏记集》的记载,支谦翻译了包括《维摩诘》、《大般泥洹》、《法句》、《瑞应本起》等在内的二十七部经书,这些译著被赞誉为准确传达了佛教圣义,且文辞典雅。而《高僧传》则记载,从吴黄武元年至建兴年间,支谦共翻译了《维摩》、《大般泥洹》、《法句》、《瑞应本起》等四十九部经书,同样以文辞优美、意义深远著称。沈奥同学指出,关于历代佛经目录所记载的支谦译经数量及其差异,可以参考李周渊在《五台山研究》2023年第2期上发表的《隋唐经录与〈出三藏记集〉的差异——以支谦译经为例》一文。此外,吕澂经过考订认为支谦实际翻译的经书有29部;而《大正藏》则收录了23部被定为支谦所译的佛经。然而,那体慧(Jan Nattier)对《大正藏》收录的支谦译经提出了异议。她认为,《大正藏》所列的23部中,《大明度经》《佛说阿弥陀三耶三佛萨楼佛檀过度人道经》《佛说老女人经》《了本生死经》《佛说四愿经》这五部经书的译者并非支谦,而《般泥洹经》和《法句经》等两部经典则应当归于支谦名下。据此,那体慧认为支谦实际翻译的经书数量应为20部。
最后,沈奥同学向我们介绍了海外关于支谦的研究情况。特别提及了那体慧(Jan Nattier)在支谦译经领域的贡献,并参考了李周渊在《汉语佛学评论》第七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年版,第251—281页)上发表的《那体慧支谦译经研究评述》一文。这篇文章对那体慧在支谦译经研究方面的成果进行了全面而深入的评述,为我们了解海外支谦研究的最新进展提供了宝贵的参考。
在认真听完两位同学的汇报后,黄凯老师代表与会老师对他们的表现进行了细致的点评。黄凯老师首先对两位同学的准备工作表达了高度的赞赏,认为他们在领读过程中展现出了认真、细致且扎实的态度。接着,黄凯老师结合自己对文本的深入解读,为两位同学及读书会全体成员提供了进一步深入研究的宝贵建议。
他鼓励大家从概念史和思想史的角度出发,对支谦译经等问题进行深刻思考,以期形成具有独创性的思想成果。特别是在译经归属这一复杂问题上,黄凯老师希望大家能够以此为突破口,努力取得新的研究成果。
当沈奥同学就研究译经归属的方法论向黄凯老师请教时,黄凯老师给予了详尽的指导。他推荐大家参考李周渊博士论文中采用的内外并重的研究方法,即一方面通过外部对比经序、经录的记载,判定译经归属信息的可靠性;另一方面,则通过内部语言学、词汇学的分析,观察并比较不同译经者的语言特色,借助特有词汇和风格来进行经典归属的判定。
此外,黄凯老师特别介绍了国外学者常用的TCAL工具,这一工具利用计算机技术对数字化汉语佛教藏经进行统计分析,能够揭示出不同译者在用词和句法上的偏好,从而帮助研究者更加客观地理解翻译策略背后的文化逻辑与思想意图。
两位同学认真记录了黄老师的每一条建议,并表达了深深的感谢。
至此,西北大学玄奘研究院读书会第99期活动圆满结束。
(编辑:李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