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3月24日晚,西北大学玄奘研究院读书会第107期活动在线上、线下同步举行。本次读书会的主题为“读《大唐西域记》序言”,分别由西北大学历史学院学院硕士生周子菲、李佳龙与殷纪泽同学进行报告,邀请了西北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副教授谢志斌老师与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助理研究员黄凯老师担任本次读书会的评议人。西北大学历史学院李永斌副教授及西北大学哲学学院、历史学院以及中国人民大学、山东大学、暨南大学、贵州大学等高校和单位的20余名师生在线上线下一同参与了此次读书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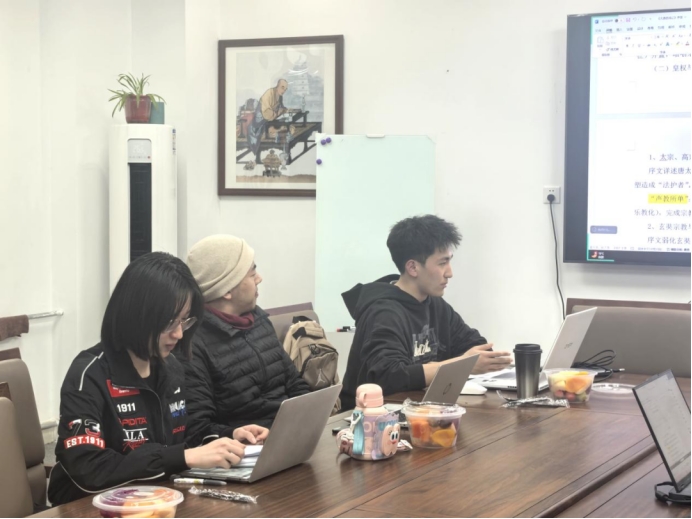
首先由周子菲同学对《大唐西域记(敬播序)》进行汇报,周子菲同学通过对文本注释进行详细解读,将内容梳理为对敬播其人与其作序的考证,敬播的政治立场,“华夏中心说”、佛教与儒道的冲突与调和等四个方面。
周子菲同学依据高田时雄的研究以及《新唐书》《旧唐书》等历史文献,对敬播的生平经历与任职轨迹进行了细致梳理。从《新唐书》可知,敬播于贞观初进士及第后,参与了颜师古、孔颖达等人编撰《隋书》的工作,并由此迁任著作佐郎,兼修国史。而《旧唐书》虽在其任职记载上存在部分差异,但综合来看,敬播序的创作年代可确定为高宗初年以前。至于敬播为《西域记》作序的缘由。周子菲同学结合《旧唐书》中敬播在永徽初拜著作郎后 “与许敬宗等撰西域图” 的记载,合理推测在编撰《西域图志》的过程中,《大唐西域记》成为重要参考资料,敬播在熟读之后为其作序。这一考证过程,不仅展现了对历史文献的严谨解读,更体现了从历史背景出发探寻文本创作动机的学术思路。
在分析敬播的政治立场时,周子菲同学指出,敬播通过 “苑十洲而池环海” 等表述,巧妙地将神话地理与现实疆域相类比。“十洲” 在道教文化中代表仙境,“环海” 可追溯至《山海经》中的 “大壑” 或佛教的 “咸海” 概念,这种类比赋予了唐朝疆域神圣性与永恒性。唐朝凭借征服西域、开通丝路的功绩,实际控制范围延伸至中亚,敬播在序文中运用神话修辞,将这一现实转化为 “德被四海” 的盛世图景,同时将道教仙境与佛教圣域并置,生动地体现了唐朝对多元文化的包容与统合,强化了唐朝作为 “天下共主” 的意识形态。
此外,敬播还通过对玄奘西行的叙事,将佛教圣域纳入唐朝的 “功德地理” 体系。在序文中,玄奘西行被描述为 “资皇灵而抵殊俗”,取经成就被归功于唐太宗的 “神武” 与 “明德”,这不仅彰显了唐朝作为佛法护持者的重要角色,也意味着玄奘记录的印度佛教遗迹。如那烂陀寺、鹿野苑等,被纳入唐朝文献体系,成为 “声教所暨” 的象征,有力地证明了唐朝文化影响力已超越地理边界。同时,敬播还运用佛教术语,如 “肉骨豺狼之吻”“还魂鬼蜮之墟” 来美化唐朝的边疆治理,进一步强化了唐朝统治的合法性。
在探讨 “华夏中心说” 方面,敬播序从多个维度进行了阐述。其一,以 “德” 为核心,将唐朝的统治合法性归因于道德教化与武力统一的有机结合。“德被万物”“扫搀抢而清天步”“掩遐荒于舆地” 等表述,强调唐朝的疆域扩张是道德感召的结果,而非单纯的武力征服,暗示唐朝的 “德” 具有超越地理边界的普适性。其二,引用汉代 “藁街” 这一典故(外族臣服后聚居长安的街道),通过唤起历史记忆,强化了唐朝 “四夷来朝” 的盛世景象,彰显了唐朝政治权威对 “异类” 的统摄力。其三,面对天竺 “圣贤叠轸”“经藏石室” 的情况,敬播强调玄奘 “周流多载” 后携经归唐且 “有诏译焉”,这一表述暗含了对印度佛教地位的消解与替代。随着印度佛教的逐渐衰微以及中国佛教的崛起,唐代借助《大唐西域记》等文本重新定义了 “中心” 概念,序言中称天竺 “壤隔中土”“《山经》莫纪”,以地理隔绝暗示其文化地位的边缘化。其四,描述西域诸国 “顿颡知归”“梯山实奉贐”,将政治臣服与文化认同紧密绑定,构建起 “华夏 - 蛮夷” 的等级秩序。“袭冠带而成群” 以衣冠制度象征文明开化,暗示西域诸国通过归附唐朝获得了更高的文化身份。谭世宝的研究指出,南北朝至唐代的佛教中心转移与 “中国” 概念的扩展密切相关,华夏礼制成为衡量 “佛国” 的重要标准,西域使节在宫廷中的朝拜仪式被赋予文化皈依的象征意义,进一步强化了唐朝作为教化输出者的优越地位。其五,以 “苑十洲而池环海” 自诩,借助《海内十洲记》的仙境隐喻,将唐朝疆域与神话空间叠加,塑造出 “小五帝而鄙上皇” 的帝国神话。古代中国的 “天下中心观” 常常借助神话地理来增强说服力,敬播序通过 “十洲” 意象,将唐朝的实际统治与神话中的 “中央之国” 相重合,构建起不可挑战的文化霸权。通过这些政治话语、宗教叙事与神话修辞,唐朝被塑造为道德、宗教与文明的三重中心,这一叙事背后反映了佛教中心转移的历史现实与华夏中心观的理论合流,同时也是唐代通过佛教本土化与知识垄断完成文化霸权建构的体现,最终使得 “天竺中心论” 逐渐被 “华夏中心论” 取代,中国从佛教的 “边地” 升格为 “佛国”,成为亚洲文明秩序的新核心。
周子菲同学指出在佛教与儒道的冲突与调和部分,敬播序体现出显著的佛儒调和倾向。序文中称天竺 “圣贤以之叠轸,仁义于焉成俗”,这是将佛教起源地天竺纳入儒家 “圣贤”“仁义” 的话语体系,这种表述策略自法显的《佛国记》以来,便是佛教徒常用的方法,通过将佛教核心价值与儒家伦理相勾连,如将 “慈悲” 等同于 “仁”,“持戒” 类比 “礼”,有效消解了儒佛对立。陈寅恪曾指出,唐代佛教高僧常常 “假借儒典文句,以证释教义理”,敬播序中的 “总异类于藁街,掩遐荒于舆地” 表述,明显模仿了《尚书・禹贡》的 “五服” 体系,将玄奘西行纳入儒家 “王者无外” 的政治想象,并且以 “国典”“故老” 为考据依据,契合了儒家 “述而不作” 的史学传统。序末强调 “我大唐之有天下也,辟赛宇而创帝图”,将佛教传播与唐王朝的 “德被四海” 紧密联系起来。汤用彤在《隋唐佛教史稿》中提到,玄奘取经活动被包装为 “皇灵所庇” 的国家工程,这种 “佛教中国化” 策略成为缓解儒佛紧张关系的关键。
同时,敬播序也体现了佛道对立特征。“隐括众经,无片言而不尽” 与 “谬肆力于神池” 形成鲜明对照,玄奘开创的法相宗特别强调 “转识成智” 的理性思辨,而道教注重 “炼气存神” 的实践,二者在方法论上存在显著差异,这种差异在序言中通过 “博考精微” 与 “徒采” 的措辞对比得以彰显。此外,该序创作于贞观二十二年(648 年),当时唐太宗晚年倾向道教,佛教急需争取话语空间。序中 “德不被物,威不及远” 看似批评前朝,实则是对当代的警示,传达出只有支持佛教才能实现 “总异类于藁街” 的大唐盛世气象的观点。

李佳龙同学对《大唐西域记(于志宁序)》的汇报从版本及争论、玄奘西行求法背景、序文中的儒释交融与权力叙事等三个部分展开论述。
在版本及争论方面,李佳龙同学介绍了《大唐西域记》现存的三篇序文,即敬播序、于志宁序和玄奘自序。其中,于志宁序在版本流传过程中存在诸多争议。在唐代通行的版本中,大多附有敬播序,然而北宋福州始刻的东禅寺版《大唐西域记》却没有敬播序,取而代之的是记有 “尚书左仆射燕国公” 的序文。在众多后世版本,如《明南本》《明北本》《径山本》《中本》《酬本》以及《金陵本》等中,虽都记载了这篇序文,但多数版本仅提及 “尚书左仆射燕国公制”,并未明确指出 “燕国公” 就是于志宁。由于唐代有两位著名的 “燕国公”,除了于志宁(599 - 665),盛唐时期的张说(667 - 730)历任三朝宰相,更负盛名,因此嘉兴藏本曾补 “尚书左仆射燕国公张说制”。不过,《中本》明确记载 “尚书左仆射燕国公于志宁”,季羡林先生在《大唐西域记校注》中也指出,诸本中唯有《中本》有 “于志宁” 三字,《金陵本》从其增补,而《径山本》在 “燕国公” 下补 “张说” 二字属于年代不符、张冠李戴的错误。此外,《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记载唐高宗命令尚书左仆射燕国公于志宁等重臣修订玄奘新译出的经典,《大唐西域记》也在修订之列,这进一步证明了此序为于志宁所作的合理性。
接着,李佳龙同学对玄奘西行求法的背景进行了深入分析。南北朝至隋唐时期,佛教界因翻译差异与师承不同,形成了南北学派对经典理解的严重分歧。《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一记载:“去圣时遥,义类差舛,双林一味之旨,分成当现二常;大乘不二之宗,析为南北两道”,这种分歧导致教义急需统一。同时,玄奘师承印度瑜伽行派,但中土对唯识学核心论典《瑜伽师地论》的理解存在不足,玄奘西行的重要目的之一便是求取该经典,以厘清 “八识”“转依” 等理论。《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一有言,“法师既遍谒众师,备飡其说,详考其理,各擅宗涂,验之圣典,亦隐显有异,莫知适从,乃誓游西方以问所惑,并取《十七地论》以释众疑,即今之《瑜伽师地论》也。” 再者,隋唐前佛经多由胡语转译,存在诸多缺陷,如鸠摩罗什译本虽流畅但删减较多,真谛译本则晦涩难通,这也促使玄奘决心西行求法,“或恐傳譯踳駁,未能筌究,欲窮香象之文,將罄龍宮之目”。
在总结与扩展部分,李佳龙同学对序文中的儒释交融与权力叙事进行了深刻阐述。在儒家话语的渗透方面,序文引用 “帝轩提象”“大舜宾门” 等典故,将玄奘世家与儒家圣王相类比,将其纳入 “世济之美” 的士族传统,从而淡化了玄奘出家的 “离俗” 色彩。同时,借助 “陈门双骥”“汝颍奇士” 等事迹,以地域文化符号如汝颍多士,将玄奘兄弟比附为儒家贤臣,暗示高僧在帝国中的精英地位。此外,“宝车丹枕,实出世之津途” 将佛教解脱工具如丹枕指经卷与士大夫的 “宝车”并置,体现了宗教修行与世俗功业的兼容,实现了神圣性与世俗性的调和。
在皇权与佛法的共谋叙事方面,于志宁序文详述唐太宗与唐高宗二帝为玄奘作序题记,将帝王塑造为 “法护者”,借助佛教话语巩固了帝王的世俗统治权威。“声教所单” 的表述将佛教传播等同于唐王朝的 “声教”,完成了宗教行为向政治功绩的转化。同时,序文弱化了玄奘 “偷渡出关” 的史实,转而强调 “奉诏翻译”,将其纳入官方叙事体系,通过 “陋博望之非远” 等表述,将玄奘西行塑造为对张骞、法显的超越,掩盖了其民间行者的身份,代之以 “官方使臣” 的集体记忆,消解了宗教行动对帝国边界的潜在威胁,重构了玄奘宗教与政治的双重身份。

殷纪泽同学聚焦于《大唐西域记》玄奘法师自序展开分享。他首先探讨了这篇自序的定位问题,并通过辨析选择了赞同季羡林先生的观点,即应将其视为《大唐西域记》整本书的一部分,而非孤立的序言。这一观点主要基于两个重要依据:其一,宋元以来的版本大多将这部分序言作为开篇进行排版,并未与前两篇真正意义上的序言放在一起;其二,像《法苑珠林》这样重要的佛教经典,在引述这部分内容时,将其当作《大唐西域记》的正文,而非序言。这表明在古代佛教学者的认知中,玄奘的这篇序言应属于正文的一部分。
殷纪泽同学进一步概括出自序可分为五个段落。在第一段中,玄奘详细阐述了《大唐西域记》的成书价值,涵盖了其在政治和文化方面的重要意义,以及写作这本书的契机。随后的四段内容,则交代了《大唐西域记》中一些重要的地理历史史实。
在成书背景方面,殷纪泽同学依据《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的记载,深入分析了唐太宗关注西域风土的军政考量。贞观十八年,玄奘在回国途中被于阗国王挽留时,唐太宗致书玄奘“欢喜无量,可即速来与朕相见”,这不仅体现了唐太宗对玄奘个人品格和成就的高度推崇,更反映出他急于了解玄奘在西域的见闻,以便制定相应的军事策略。季羡林先生在《佛教十六讲》中指出,当时太宗正为征伐辽东备战,急需知晓西域的一手情报,这充分说明了《大唐西域记》在政治军事层面的重要性。同时,殷纪泽同学还强调了《大唐西域记》作为盛唐载记的历史政治意义,玄奘在《进〈西域记〉表》中提到 “窃以章亥之所践籍,空陈广袤;夸父之所陵厉,无述土风。班超侯而未还,张骞望而非博。至于玄奘所记,微为详尽,其迂辞玮说多从翦弃,缀为《大唐西域记》一十二卷,缮写如别”,表明该书在记录西域风土人情方面超越了前人,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
最后,殷纪泽同学介绍了《大唐西域记》在唐代的著录和流传情况。他整理道,道宣是该书的有力推动者,麟德元年(664),他编撰《大唐内典录》,两次著录《大唐西域记》,一次是在《皇朝传译佛经录第十八》中,将其列为玄奘译述大小乘经论六十七部的最后一部,另一次是在《历代道俗述作注解录第六》中著录了包含《大唐西域记》在内的佛教文献。窥基法师在《大乘法苑义林章》中也多次引用《大唐西域记》,如《大乘法苑义林章・第一结集缘起》就汇集了《结集三藏传》《付法藏传》《大智度论》《真谛三藏部执疏》《大唐西域记》第九卷以及《四分律》等内容。在初唐时期,《大唐西域记》并未受到时人的特别重视,仅在佛教僧众间有所流传,未得到唐太宗、高宗以及文人士族、权贵精英的广泛关注。然而,到了中唐之后,情况发生了显著变化,该书的流传越来越广,影响力越来越大,笔记小说、韵文诗书、佛教文献等大量著录、引用《大唐西域记》。唐之前关于西域的文献众多,如释道安《西域志》、释智猛《外国传》、裴矩《西域图记》、释彦悰《西域记》等,但大多已亡佚,唯有玄奘的《大唐西域记》凭借其独特的魅力广为流传,不仅在唐宋、元明清史学目录和历代藏经中皆有著录,还在日本历代流传抄本,其影响力超越了时代与疆域。
在本期读书会中,周子菲同学对《大唐西域记(敬播序)》从敬播作序考证、政治立场、“华夏中心说” 以及佛教与儒道关系等方面进行了细致解读;李佳龙同学针对《大唐西域记(于志宁序)》,在版本考证、玄奘西行背景以及序文中的儒释交融与权力叙事等方面展开深入分析;殷纪泽同学则聚焦玄奘自序,探讨了其定位、成书背景和流传情况。三位同学的汇报角度各异又相互补充,共同构建起对《大唐西域记》序言较为全面的理解框架,这种深入的研究和精彩的展示得到了黄凯老师的充分认可与高度评价,称赞他们准备充分、内容详实、逻辑清晰。
在肯定之余,黄凯老师也指出了几位同学讲读过程中存在的一些小问题。对三位同学的汇报进行点评之后,黄凯老师引导参会师生思考关于阅读《大唐西域记》的几个重要问题:为什么读这本书?要怎么读?要读出什么?不同的研究者由于学术背景和兴趣不同,对《大唐西域记》的关注点也会有所差异。如从事西域地理研究的学者可能更关注书中的地理信息,而研究佛教的学者则会聚焦于佛教相关内容。因此,在阅读之前,明确自己的研究方向和目的至关重要,这样才能在阅读过程中有针对性地筛选和分析信息,提高阅读效率和研究质量。
谢志斌老师结合自己的研究经验,分享了阅读历史文献的三个方向,为师生们提供了具体的研究方法指导。

第一个方向是关注字音字义和文章中的典故。尽管《大唐西域记》的序言在某些宏观学术问题上可能挖掘空间有限,但逐字逐句研读可以让研究者了解大量中国中古时期的文本书写典故,这对于积累知识、培养学术基本功极为重要。第二个方向是尽可能结合现有的学术研究成果。在阅读过程中,了解学者们对相关文本的研究讨论,可以让研究者站在巨人的肩膀上,避免重复劳动。通过学习前辈学者如何使用资料进行论证,最终得出结论,年轻学者能够逐渐掌握学术研究的方法和技巧,提升自己的研究能力。第三个方向是在掌握现有研究的基础上,尝试发现新的问题。学术研究是一个不断探索和前进的过程,即使是一些被广泛研究的问题,也可能存在尚未解决的部分。研究者在充分了解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如果能够结合自身兴趣和学术敏锐性,发现新的问题,并尝试进行深入研究,将有可能取得创新性的学术成果。这需要研究者具备扎实的学术基础、敏锐的洞察力和勇于探索的精神。
谢志斌老师还特别强调,对于研究生来说,阅读《大唐西域记》要有明确的学术目标,要 “进得去,出得来”。“进得去” 包含三点:文本文字、审美意境、心胸境界。通过扎实的训诂、考据和对文章意境的体会,掌握文本的内涵和精髓。“出得来” 也要求三点:问题意识、学术视野、学科理论。要求读者不能仅仅停留在对文本的理解上,还要从学术研究的角度出发,运用学者的视野去分析问题,在宗教学、历史学、文献学、区域国别学等不同学科的理论和范式的指导下进行进一步的研究,并最终形成学术成果。
至此,西北大学玄奘研究院读书会第107期活动圆满结束。
(编辑:华也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