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4月21日晚,西北大学玄奘研究院读书会第111期活动在线上、线下同步举行。本次读书会汇报的内容为《大唐西域记》卷一的最后一部分及卷二的印度总述部分,由西北大学历史学院学院硕士生邹景发与华也靓同学进行报告。西北大学历史学院李永斌副教授、西北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谢志斌副教授及西北大学历史学院、哲学学院以及中国人民大学、山东大学、北京师范大学、贵州大学等高校和单位20余名师生在线上一同参与了此次读书会。
首先由邹景发同学围绕《大唐西域记》第一卷中的部分内容进行领读与汇报。在对文本内容进行正式解读前,邹景发同学先对吐火罗人迁徙史的背景进行了补充。关于吐火罗(Tochari)人的来历及其迁徙发展的历史目前尚无定论,邹景发同学采用《塞种史研究》(余太山,商务印书馆,2012)、《吐火罗史研究》(王欣,商务印书馆,2017)等著作中,主张吐火罗是大夏的说法。据研究,吐火罗人作为原始印欧人群的一支,应当起源于中东欧,约于公元前3000年自中东欧东迁,公元前2000至前1000年进入塔里木盆地。考古证据显示,东欧颜那亚文化与中国克尔木齐文化及罗布泊古墓沟文化存在关联,印证了早期迁徙轨迹。据学者推测此时吐火罗人分南北两支:北支定居库车、焉耆,从游牧转向定居,语言保留更多印欧特征;南支经罗布泊至敦煌,残留在南疆的人群在安得悦古城一带形成一个聚居地,经学者考证应当就是玄奘法师归国时在《大唐西域记·卷十二》中记载的“睹货逻故国”。这支吐火罗人的大部分又继续东迁,至河西的敦薨(敦煌),也可能到达了陕北、晋南,即汉文文献记载的“大夏”。春秋时期,晋南吐火罗人因齐国扩张西迁河西,与当地吐火罗人会合。"敦煌"地名或源自其族名简译。但汉文文献对他们的认识也非常模糊,并未意识到他们与“大夏”的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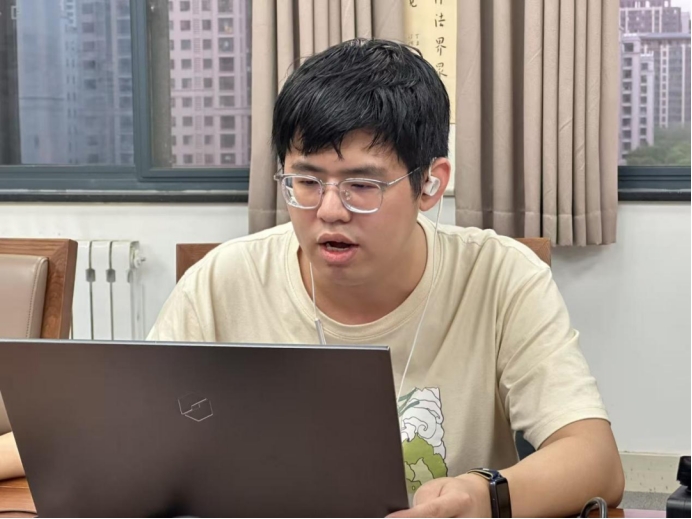
秦汉之际,河西吐火罗人受月氏、乌孙挤压,西迁伊犁河-楚河流域。公元前201年,大月氏受冒顿单于打击后也西迁至此,吐火罗人又被迫迁徙至锡尔河以北流域。公元前141年前后,吐火罗四部联合斯基泰部落终结希腊人在巴克特里亚的统治,吐火罗人的大迁徙也就此告一段落,张骞仍称其为“大夏”。公元前130年大夏被大月氏征服,形成五翕侯分治格局。贵霜翕侯最终崛起建立贵霜帝国,对于国王丘就却等翕侯统治者的族属在学术界有争议,但总之,贵霜帝国的国家上层应当由吐火罗人和大月氏人构成,境内均以土著化了的吐火罗人和吐火罗化了的巴克特里亚人。此后还有迦腻色伽建立的第二贵霜王朝,迦腻色伽是弘扬佛教的重要人物,传说他有鉴于佛教派别争论严重,曾促成佛教第四次结集。此后吐火罗地区历经萨珊波斯、嚈哒、突厥统治,唐代设月氏都督府。7世纪后期阿拉伯势力入侵,吐火罗叶护政权延续至8世纪中叶,安史之乱时曾派兵助唐,最后被阿拔斯王朝攻灭。
在此基础上,邹景发同学展开了对《大唐西域记》中所记载的覩货逻国故地的详细介绍,在地图上标志出大致的范围,以如今的杜尚别为例,辅以温度图与气温图,介绍其气候。指出佛陀接纳雨安居的原因是爱护生命。但实际上也应当是当地雨季难以出行的必然结果。汉传佛教的安居制度可追溯至后秦时期,以农历四月十六日至七月十五日作为安居期。如玄奘所言,睹货逻故地独特的安居时期也与当地的气候有关。关于其容貌,新疆考古证据表明吐火罗人的外貌特征都是黄褐或棕褐头发、蓝眼睛、高鼻,具有原始印欧人特征,头骨类似北欧型。但在巴克特里亚的这一支吐火罗人相比北支,经历了更多的迁徙历程和民族融合,原始印欧人的体貌特征应当保存较少。关于语言,邹景发同学根据此前介绍的吐火罗迁徙史相关的观点,指出巴克特里亚的吐火罗语,与甲种吐火罗语(焉耆语)都应当是“真吐火罗语”。巴克特里亚语是唯一一个使用基于希腊字母的书写体系的中古伊朗语。对于吐火罗钱币,邹景发同学根据苏俄学者的研究指出,当时吐火罗地区流行的钱币主要是模仿萨珊波斯银币铸行的银币,其上有巴克特里亚文、粟特文或装饰性纹样的戳记。但在细节上,这些模仿萨珊波斯银币铸行的银币其钱币铭文语言,君主肖像风格等都已经发生了变化。
越过铁门关,第一个到达的是呾蜜国。首先,邹景发同学指出拿梵文作标准来衡量音译名词是不合适的,接着对呾蜜国进行了具体介绍,在地图上标注其位置,并根据考古发现指出这里有公元前2世纪希腊人的砦堡,以及贵霜王朝时期的佛寺、佛塔等。出土的陶器上有许多与巴里黑、苏尔汉一科塔等地出土文物上相同的婆罗谜字体和怯卢字体铭文,恐系吐火罗人的文化遗存。此后,邹景发同学又依次将赤鄂衍那国、忽露摩国、愉漫国、鞠和衍那国、镬沙国等国家在地图中进行标注,与《新唐书·地理志》等文献及中所记载内容及马迦特的考证进行对比,更加直观地展现出《大唐西域记》中所载各国的地理位置。
在睹货逻故国,玄奘第二个来到的国家是活国,《大唐西域记》中并没有过多记载,邹景发同学在《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中找到了相关的记叙,并进行了补充。关于活国,《旧唐书·地理志》作遏换城,《新唐书》作阿缓城。相当于波斯语文献的Valvālij,即今Warwāliz。在昆都士附近。为西突厥吐火罗叶护政权治所,唐以其地置月氏都督府。可能原属五翕侯属地。在介绍缚喝国时,邹景发同学同样以《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加以补充,并结合《吐火罗史研究》指出,吐火罗人建大夏国,这里作为都城也是他们活动的中心地区之一。玄奘称“其城虽固,居人甚少”,表明至唐初时,经过数百年战乱的纷扰,这里的吐火罗人可能大部分已徙居他处。西突厥征服吐火罗斯坦以后,以阿缓城为中心曾出现了一个吐火罗国,亦表明吐火罗人活动中心的某些变化。在介绍胡蹇健国时,邹景发同学同样补充了《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中玄奘法师在此处做客的经历,并且指出希腊托勒密的《地理志》与亚美尼亚文《波斯地志》都提到这里出产良马。最后,邹景发同学结合地图梳理了玄奘法师在睹货逻故国可能到过的所有国家,并按顺序进行了路线的展示。
接着由华也靓同学对《大唐西域记》卷二的印度总述的前半部分进行分享汇报。在探讨关于印度的称呼以及其名称的含义前,其先对中印在唐前的交流历史进行了回顾,主要参考了季羡林先生的《中印文化交流史》。华也靓同学提到,季羡林的《中印文化交流史》将中印文化交流的历史分为七个阶段:一、“滥觞(汉朝以前)”;二、“活跃(后汉三国25-280年)”;三、“鼎盛(两晋南北朝隋唐265-907年)”;四、“衰微(宋元960-1368年)”;五、“复苏(明1368-1644年)”;六、“大转变(明末清初)”;八、“涓涓细流(清代、近代、现代)”,并在书中将中印文化交流的活跃期,即后汉三国时代定为中印两种精神文化的撞击和吸收阶段;将鼎盛期两晋南北朝隋唐时代定为两种文化的改造和融合阶段;将衰微期宋元时代定为两种文化的同化阶段。中印交往的起点并无可靠的文字记载,只能从考古、天文与神话传说中进行探索。中国汉代正史中有关印度的记载是中印关系有正式记载的开始,在《史记》卷一一六《西南夷列传》中有公元前一三七一八年张骞在大夏看到了中国蜀布和邛竹杖,并且得知是从东南身毒国而来的记载。《前汉书》卷二十八下《地理志》中关于古代中印以及其他国家交通的记载,受到中外学者极端的重视。其中地名之一的“黄支国”,绝大多数学者认为就是印度的建志补罗,也就是位于印度东海岸的康契普腊姆(Conjevaram),这是中印古代海路交通可靠的证据。《后汉书》卷一一八《西域传》,特别为天竺立传,并对印度各方面的情况描写具体,可见此时中国对印度的了解程度已大大增加。接着华也靓同学又对“印度”含义及词源等进行具体分析,并结合唐高宗时期义净法师的《南海寄归内法传》,相对玄奘对于“印度”含义的解释提出了不同意见。同时,其又结合文本与地图展示了当时印度的疆域范围,推测出玄奘所记“形如半月”具体所指印度的哪一部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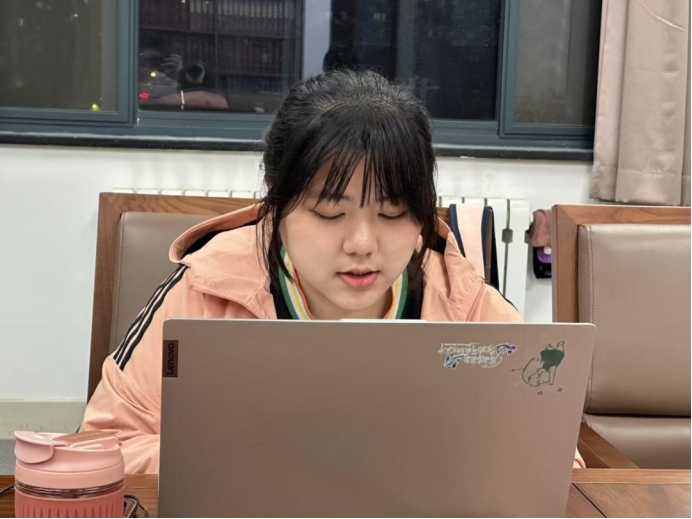
此后华也靓同学对文本中所提到的数量单位进行了具体的解读,又简要介绍了印度的时间单位及时节变化。在对印度建筑一条进行解读时,注意到印度建筑雕刻工艺的精美及城市布局的规划,并展示了摩亨佐·达罗遗址。同时结合第六条衣饰方面,对印度手工业发展进行合理推测。她认为,玄奘记述城市建筑的规模和城市户口时没有说到手工业,这可能由于城市里没有专门从事手工业或至少没有能引起他注意的那种手工业,也可能手工产品主要来自农村公社。但根据马克思关于印度农村公社的记述可作参佐,“农村手工业与农业的联系,是印度农村公社的特点。农村中有一个铁匠,一个木匠,制造与修理各种农具;一个陶土工,制造村民使用的各种容器;一个银匠等等;他们多由公社全体出费来维持。这种手工制造业不可能有分工,因为铁匠、木匠等的生产品的市场是不变的,至多不过依照公社大小,由一个铁匠,一个陶工等等,增加为二个或三个。”(《资本论》卷一,人民出版社,431页)另一方面,从玄奘所记手工业产品,可以想见印度的手工业。如服用品:“桥奢邪者,野蚕丝也;刍摩衣麻之类也;顩(虚严反)钵罗衣,织细羊毛也;褐刺缡衣,织野兽毛,细耍可得缉绩,故以见珍而充服用”。从这些衣料看来,可见已有丝织、麻织、毛织等纺织工业。从文本中还可以看出,印度此时衣饰有帔搭的特征。在已公布的印度和巴基斯坦等地区考古资料显示,大量的佛教雕刻和壁画人物中有身着帔帛例证,说明在公元前1-2世纪穿戴帔帛已相当普及。华也靓同学提到可以关注印度衣饰对唐代服饰的影响,如妇女着装逐渐开放,佛像中也多袒露身体;敦煌壁画中飞天女神形象,富有人体美的美感,颜色更加多彩,图案祥瑞化。
在介绍印度馔食时,华也靓同学分析印度非常注重教规,注重洁净。从前面介绍的古城发掘出的大浴室遗址来看,印度注重沐浴盥洗有由来已久的传统,可能也与其宗教信仰有关。她尤其关注了玄奘对“杨枝”的记载。在《十诵律》《五分律》《四分律》等等都有关于杨枝的记录,在《高僧传》中还有释玄畅杨枝击沙以退灭佛追兵的记载。实际上,玄奘《大唐西域记》及其前译佛经中所谓的“嚼杨枝”应该称作“嚼齿木”,这是古代印度通行的一种揩齿刮舌以清洁口腔及牙齿的方法。玄奘在《大唐西域记》中所用的称呼只是沿用汉译佛经中的习称。我国早期的汉译佛经中,“齿木”多译作“杨枝”。古代印度用作“齿木”的材料有多种,可以是“杨枝”,但不限于“杨枝”。除了佛祖的明示之外,对齿木的材料问题,义净法师在其所着《南海寄归内法传》卷一中也曾对“嚼齿木”有详细的说明和辩证。义净坚持用“嚼齿木”而不用“嚼杨枝”,其认为在古印度用作齿木的材料是因地制宜,并且专门辩证他所以取用“齿木”这一名称而不作“杨枝”的原因。最后还可以看出“嚼齿木”是五天竺地区的日常故事,“三岁童子,咸即教为”。除了古代印度有嚼齿木护齿的习俗之外,其他一些受到印度和佛教影响较大的地区也有这种习俗。《隋书·南蛮传》记述了“真腊国”使用杨枝净齿的情况,且这一风俗也传到了爪哇岛、阿拉伯、东亚等各地。
接下来,华也靓同学介绍了印度文字的状况。印度系文字主要有婆罗米文、佉卢文及其他衍生文字。现存最早的用这些文字的记录是孔雀王朝阿育王(前264—前223)的石柱铭文。有学者认为,婆罗米文可能是在阿育王本人的指导下创制于孔雀王朝时期,佉卢文可能于公元前4世纪甚至公元前5世纪产生于西北印度地区。同时华也靓同学指出,玄奘法师记述与中国史官职掌相似,这是以中国习惯观察印度。此后对印度的教育情况进行了介绍,分析文本可知,相对于种姓制度与婆罗门的特权,此时的印度教育反映出了一种民主与普遍性,无论是儿童章句的启蒙,还是五明大论中所学有工巧及医方等内容,都反映出了教育的内容还是较为多样的,这应该也与佛教的发展有关。实际上,在佛教改革教育制度,破除等级制度,主张人人都有受教育的权力后。这一主张,也吸引了众多的婆罗门教徒。以此为契机,婆罗门徒开始参与到各种职业中去。一些城府创办佛教教育场所,广招通宿生。入学不受种姓限制。对于文中所提到的“四吠陀论”,玄奘将其概括为寿、祠、平、术。这引起了一些学者的议论。印度学者 D.K.Gupta 在他的著作 Society and Culture in the Timeof Dandin(《昙丁时代的社会和文化》)中谈到昙丁时代的教育。昙丁在所着 Avantisundarikathā中列举了Rajavahana 等王子要学习的学科,除《吠陀》和《吠陀》分支外,还有副吠陀:Ayurveda(医学)、Dhanurveda(军事)、Gandharveda(音乐)和Sthapatya(建筑),以及Itihāsaveda(指的是两大史诗和古事记)。此外,还要学习《法论》和《爱经》等等。因此,季羡林先生认为玄奘以副吠陀代正典:《阿由吠陀》(寿命医学)替代了《梨俱吠陀》。最后,华也靓又结合文本介绍了当时印度佛教的发展状况。
在总结时,华也靓同学提出了《大唐西域记》推动并反映了中国对天竺认识的加深。《后汉书》《旧唐书》《新唐书》《大唐西域记》对天竺的记载侧重各异,详略及用语方式上也各有差别。从《后汉书》到两唐书可看出明显的承袭、发展痕迹,同时也可以看出中原王朝对于天竺国由陌生而逐步了解、认识的探索过程。《大唐西域记》内容最为翔实丰富,且因是行纪体裁,体制、侧重上与正史均有差别。这其中反映出了正史与私人游记、笔记的不同记述风格。这种官方与私人的话语差别互为补充,又相互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后人对于域外文化的认知和理解。也有相关文章如吴昊天《历史叙述中的中印交通史——<后汉书>、两唐书及<大唐西域记>中对于天竺记载的文本比较》(《学理论》2013年第22期)的发表。
最后,沈奥同学进行了补充与分析。首先,他指出数量一节中关于单位长度的参照物是值得注意的,如“肘”“指”参考了人体部位,“宿麦”参考了植物即冬小麦,“虱、虮”参考的是动物,“牛毛、羊毛、兔毫”用的是动物毫毛,兔毫也可与中国神话中西王母升天的信仰所联系。其次,他还关注到了衣饰一节中提到的印度关于“染其牙齿,或赤或黑”的习俗,在佛经中有对于黑齿梵志人物的记载,唐代还有著名将领黑齿常之,黑齿或与百济族习俗有关。另一方面,嚼食槟榔也会染黑牙齿,而槟榔也是佛教五大圣树之一,这或许也是印度染齿的原因之一。关于槟榔文化史研究,沈奥同学也列出书目可供参考,如林富士的《红唇与黑齿:纵观槟榔文化史》(三民书局,2023)和曹雨的《一嚼两千年 : 从药品到瘾品,槟榔在中国的流行史》(中信出版集团,2022)
由于时间限制,《大唐西域记》卷二印度总述的剩余部分留待下一次读书会继续阅读与分享。至此,“西北大学玄奘研究院读书会”第111期活动圆满结束。
(编辑:华也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