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5月26日晚7点,西北大学玄奘研究院第115期读书会在线上、线下同步举行。本次读书会汇报的内容为《大唐西域记》健陀罗部分,由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硕士生唐箫雅与邹景发同学进行报告。西北大学历史学院李永斌副教授、区域国别学院谢志斌副教授、陕西省社科院黄凯老师,以及西北大学历史学院、中东研究所、哲学学院、文学院及贵州大学、内蒙古师范大学、温州佛学院等高校和单位20余名师生在线上一同参与了此次读书会。
首先由邹景发同学围绕《大唐西域记》第一卷中的部分内容进行领读与汇报。邹景发同学先是对健陀罗进行了概述。他从健陀罗名称的由来进行考证,指出健陀罗国是梵语Gandhāra的音译,即托勒密《地理志》记载的Gandarae。在我国文献中,有干陀罗(《洛阳伽蓝记》卷五),小月氏、干陀(《魏书·西域传》)、月氏国(《高僧传·昙无竭传》)、犍陀罗、建陀罗(慧超《往五天竺国传》)等译法。现通常译为犍陀罗。其意译据《华严经音义》卷三:“干陀是香,罗谓陀罗,此云遍也。言遍此国内多生香气之花,故名香遍国。”是故《续高僧传》作香行国,又有作香遍国、香风国、香洁国的。同时,邹同学就玄奘时代犍陀罗的地理方位进行了界定:其大致位于当代旁遮普的波托哈尔、 斯瓦特河谷和开伯尔山口之间包括旁遮普以北的白沙瓦和拉瓦尔品第(Rawalpindi)地区。主体区域即白沙瓦盆地,核心地区20余万平方公里。但历史上犍陀罗的范围也有所变动,如历史上的犍陀罗王国在强盛时疆域可达印度河下游,以犍陀罗艺术为代表的犍陀罗文化的影响范围则更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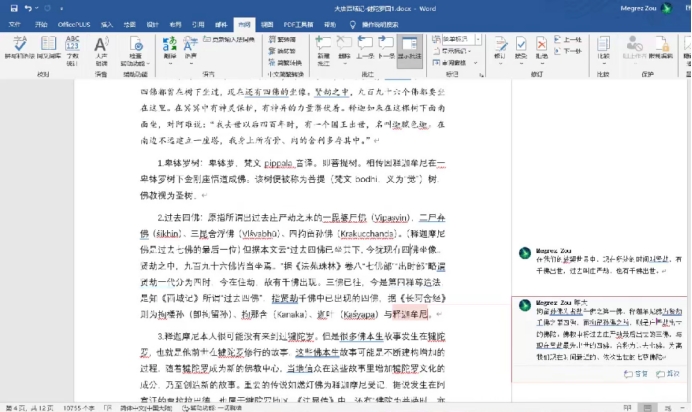
邹同学还详细介绍了健陀罗的历史变迁。犍陀罗早在公元前6世纪即已出现,是印度列国时期的十六大国之一。由于其处于亚洲心脏地带的地理位置,先被阿契美尼德王朝征服统治,孔雀王朝也征服过这里,阿育王曾派人来此弘扬佛法。后来作为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的一部分,大量希腊移民移居此地构成统治阶层。后贵霜王朝的迦腻色迦王征服这里后,其首都就位于白沙瓦。也就是说,犍陀罗是贵霜王朝的核心区域。也正因此,在玄奘看来,贵霜王朝的迦腻色迦王就是犍陀罗的国王。犍陀罗文明尤其是佛教艺术之所以名扬四海,与其受印度、波斯、希腊以及佛教等多种文化相互交融息息相关,在贵霜王朝更是达到顶峰,佛教也借此获得新的活力,从这里出发,传入中亚、东亚。其后贵霜王朝势衰,小月氏入侵,又为嚈哒(白匈奴)所灭。也正是嚈哒入侵后,犍陀罗艺术衰弱。至玄奘到达时,其地属于迦毕试国。八世纪初慧超到达时,突厥波尔哈勅懃(Barhategin)灭迦毕试而据其地,已为突厥所奴役。贵霜王朝时期这里曾是佛教兴盛之地,佛教第四次结集更是将这里的佛教推入顶峰,也诞生了众多大师。众多来自犍陀罗的僧侣更是将犍陀罗风格的佛教带入中土,对中国佛教的影响巨大。许多中国僧人来印度求法,来到这里求法后也就折返,没有深入印度腹地。玄奘称这里“多敬异道,少信正法”,可见战争对这里的佛教打击是毁灭性的。这里的异道应当就是婆罗门教。
邹指出布路沙布逻是梵语Puruṣapura音译,意“city of human”。即《法显传》的弗楼沙国,《魏书》的弗楼沙城。意译丈夫土、丈夫城,《续高僧传》卷二作“丈夫宫”。外文有记载曰Purshaur、Farshābūr等,其地经考证公认在巴基斯坦喀布尔河南岸白沙瓦市的西北地区。白沙瓦当时作为贵霜的首都辉煌一时,约公元 260 年,受萨珊王朝入侵而受到严重破坏,约560年,嚈哒(白匈奴)洗劫了整个犍陀罗地区,古白沙瓦也被彻底破坏。由于地理位置重要,后来白沙瓦又重新兴盛,成为普什图人的聚居地,莫卧儿王朝时期又是印度的西北重镇。北魏宋云到达这里时,就已经注意到犍陀罗和迦毕试国的冲突。《洛阳伽蓝记》:“自恃勇力,与罽(ji)宾争境,连兵战斗,已历三年。“玄奘至此,应当是迦毕试国取得了最终胜利。
邹同学举佛钵例将这段历史纠葛进行了串联与个案分析。佛钵,南北朝法显来此之时,就记载了这里供奉着许多佛陀的圣物、遗物,包括锡杖、佛牙、佛顶骨以及佛钵。法显详细记载了当地日常供养佛钵的情形:“可有七百余僧,日将欲中,众僧则出钵与白衣等,种种供养,然后中食。至暮烧香时复尔。可容二斗许,杂色而黑多,四际分明。厚可二分,甚光泽。贫人以少华投中便满,有大富者欲以多华供养,正复百千万斛,终不能满。”根据法显的描述,佛钵“杂色而黑多,四际分明”,符合佛教有关四天王(Lokapalas)献钵的传说:佛钵是佛陀用来盛放商人施舍食物的用具。四天王奉上各自为佛陀准备的钵,但佛陀只需要一个。为了不让四天王失望,佛陀将四个钵融合成一个,就是后来的佛钵,这一礼物象征着天王们献给佛陀的法力和神力。既然佛将四钵合而为一,自然会留下四道分界线,也就是所谓“四际分明”。当时许多中国僧人来此求法也会参与供养。佛钵最初在佛教圣地毗舍离,被迦腻色迦夺取到犍陀罗供奉。到玄奘来这里时已被波剌斯夺取,在《大唐西域记》波剌斯相关的记载中,玄奘又强调了这一信息,称:“释迦佛鉢,在此王宫”。不过校注版有校注认为这里的波剌斯不是波斯:《慈恩传》作“波剌拏(ná)斯”,《方志》作“波斯”。堀谦德谓波剌斯应作波剌拏斯(Varenasi),与卷十一之波剌斯国为二地。按卷十二《朅盘陁国》内有“波利剌斯国王娶妇汉土”,或即此波剌拏斯。总之,佛钵的丢失,存放它的位置也成为废墟,这也是当地佛教衰弱的标志。
邹同学介绍了卑鉢罗树及迦腻色迦王大窣堵波,提出释迦摩尼本人很可能没有来到过犍陀罗。但是很多佛本生故事发生在犍陀罗,也就是他前世在犍陀罗修行的故事。这些佛本生故事可能是不断建构增加的过程,随着犍陀罗成为新的佛教中心,当地信众在这些故事里增加犍陀罗文化的成分,乃至创造新的故事。重要的传说如燃灯佛为释迦摩尼受记,据说发生在阿富汗的贾拉拉巴德,也属于犍陀罗地区。《法显传》中,还有“佛陀为菩萨时,亦于此国以眼施人”的传说。这里迦腻色迦佛塔的由来,也应当是当地佛教徒创造的传说。在论及迦腻色迦对于佛教的态度时,邹同学引用芮传明先生的观点,认为他可能并非完全热衷于佛教,而是对于各种宗教信仰都兼收并蓄。现代发掘到的迦腻色迦钱币表明,他对于琐罗亚斯德教(祆教)、希腊诸神、太阳崇拜的诸神,以及印度古代诸神都很崇拜。……所以,当我们通过《西域记》来了解迦腻色的宗教信仰时,应该理解到,玄奘作为一个虔诚的佛教徒,在记载中很可能产生偏爱佛教的倾向,因而不宜毫无保留地接受玄奘关于迦腻色迦的全部说法。邹同学最后推荐了孙英刚、何平的《犍陀罗文明史》与平川彰的《印度佛教史》,希望为感兴趣的同学提供一些帮助。
接着唐箫雅同学对《大唐西域记》健陀罗国的后半部分进行了汇报讲解。对鬼母子、太子须达拿布施两儿、“一角仙人”(又称“独角仙人”)的故事进行了详述并阐述了其背后的寓意。对班尼尼的《八章》进行了叙述。《八章》是公认现存世界上最早的文法。西行取经的玄奘(602—664)在其口述的《大唐西域记》卷二里详细描述了班尼尼(玄奘称之为波你尼)的祖国犍陀罗(Gandhāra,玄奘称之为健驮逻)。他到过班尼尼的出生地娑罗闍逻(Śalātura,玄奘称之为娑罗睹逻),他的描述中没有提及班尼尼的《八章》,但对班尼尼著述“声明论”的缘起有描写,其中有两点特别值得注意:1. 班尼尼是“声明论”的作者;2. 玄奘认为他写的是一部“字书”。由这两点引发了两个问题:1. “声明论”是一本什么书,与《八章》是什么关系?2. 如果声明论即《八章》,那么《八章》到底是文法还是字书?对此唐同学对相关讨论进行了整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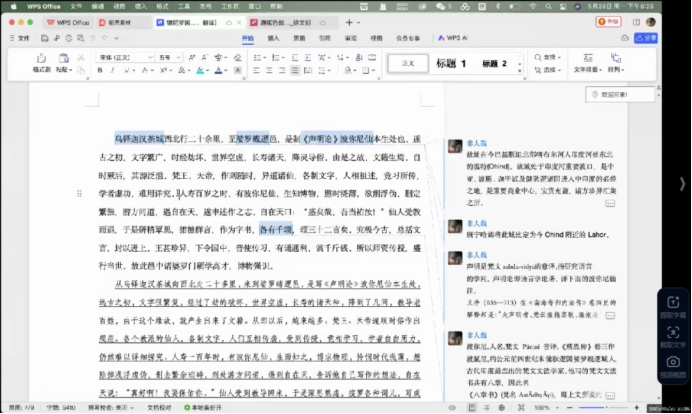
关于声明,孙良明在《中国古代语法学探究》(2005)中的解释是:“声明,梵语śabda-vidyā意译,音译摄拖苾驮,指文字、音韵、语法之学。”(160页)。然而唐代另一位西行求法的著名和尚义净(635—713)在《南海寄归内法传》卷四里的解释却是:“夫声明者,梵云摄拖苾驮,摄拖是‘声’,苾驮是‘明’,即五明论之一明也。”也就是说,śabda的意思是‘声音’,vidyā的意思是‘明瞭;明白’,二者合起来的意思是‘声音+明白’。义净没有说vidyā的引申义是‘知识;学问’。义净提到的五明论(Pañcavidyā)指古印度的五种知识或学问,声明是其中的第一种,涵盖有关语音、音乐及其符号的学问,基本可以纳入音韵和文字学的范畴,但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文法或语法。
关于班尼尼及其声明学著作,与玄奘同时代的慧立(615—?)、彦悰(627—649)在其所著《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里有记载、孙良明(同上:161)解释说,《记论》、《声明记论是》“唐僧对梵语vyākaraṇa的意译(鸠摩罗什指称为‘语法’)”,是“文字、语音、语法书之总称”。《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里有记载的“毗伽罗”和“毗耶羯剌諵”显然是vyākaraṇa的音译。解读vyākaraṇa,要从印度最古老的梵语文献吠陀(Vedas /ˈveɪdəz/,又称《吠陀经》)‘知识;智慧’说起。吠陀研究分为六个支派(vdāṅga),Vyākaraṇa是其中一支,侧重对吠陀语言形式的研究,班尼尼的《八章》被公认为vyākaraṇa研究的集大成者。吠陀的传承在吠陀时期(Vedic period,公元前约1700—约400年)仅靠口口相传,直到佛教兴起后,亦即班尼尼所处的时期,才记录成文。毫无疑问,班尼尼的研究为吠陀经典从口头传承转为书面传承做出了重要贡献,而vyākaraṇa的主要内容应当就是探究如何对吠陀的语言进行分析、记录或转写和解读。记论这一译法,虽然意思不十分清楚,却没有什么错误。玄奘把它译成《声明记论》,点明了其内容实质。
不过唐代之前,vyākaraṇa还有一种译法,即语法。孙良明(2005:151)发现,最早使用语法这一译名的是鸠摩罗什(344—413、350—409),其所译《大智度(经)论》卷四十四里有下面这段话:问曰:“何等是菩萨句义?”答曰:天竺语法,众字和合成语,众语和合成句。如菩为一字,提为一字,是二不合则无语;若和合,名为菩提。秦言无上智慧。萨埵,或名‘众生’,或是‘大心’。为无上智慧,故出大心,名为菩萨埵;愿欲令众生行无上道,是名菩提萨埵。
孙良明(同上:151—2)解释说,“所谓‘字’指音节(或字母),所谓‘语’指语词;音节组合成词(单是音节不成为词),词组合成句[…]。其中‘天竺语法’之‘语法’乃是指梵文vyākaraṇa”。问题是,作为记论研究最高成就的《八章》是一部什么样的文法或语法?玄奘将之视为字书类是否有道理?
《八章》主要由四部分内容组成。1. 音系学(Śivasūtra),班尼尼一开始先用了14行的篇幅说明梵文的音位和代表这些音位的梵文字母,关于梵语的语音学,《八章》中没有什么论述(见Robins 1997: 179);2. 构词法(Aṣṭādhyāyī),这一部分“穷尽性地”(同上:178)描写了古梵文构词法的3,959条经(sūtras,本义是‘经线’)或规则,这些经遍布各章,构成了《八章》的主体内容;3. 谓词词根分类表(Dhātupāṭha),共区分出谓词的10类现在形式;4. 名词词干分类表(Gaṇapāṭha)。《八章》中不时探讨词源问题,在讨论构词法时也用到一些句法术语,如修饰性复合(tatpuruṣa,意为attributive compound,如英文的doorknob‘门把手’)、离心性复合(bahuvrīhi,意为exocentric compound,如英文的turn–key‘转动钥匙’),但基本不涉及梵文的句法。
这样看来,鸠摩罗什所谓“语法”如果指“众字和合成语”之法,即词形法或短语法,说班尼尼的《八章》是一部语法,没有什么问题;说它是“世界上最古的一部完整的语法书”(季羡林等 1985,《大唐西域记校注》264页)也不错,因为它确实完整地描述了古梵语的形态系统和构词法,只是“它不是一般意义上梵语的一部完整文法。用现代术语的说法,或许我们最好把它说成梵语的生成形态学(generative morphology)”(Robins 1997:178)。若宾斯不把《八章》视为一部完整的梵语文法原因在于它缺了句法这一部分。
玄奘称班尼尼的著作为“字书”是因为,从中国人的传统视角来看,《八章》很像《说文解字》之类的著作。孙良明(同上:164)解释说:字界、字缘是分析派生构词法的术语。字界是梵语dhātu意译,又作语界、字元、字体,指动词词根。字缘是梵语pratyaya意译,又作语缘,指附于动词词根使变为名词、形容词之结尾部分。后字界泛指词根,字缘泛指词根之词缀、词尾等。
比较《说文解字》和《八章》,我们可以看到:1. 字书区分字的字根(即许慎所谓“文”),即部首、形旁、声旁,《八章》区分词的词干、词根、词缀;2. 二者所收字根或词根、词缀的量都比较大,都达到近乎穷尽的程度;3. 二者都对所收的字根或词根、词缀根据形式上的不同分门别类;4. 二者都分析复合字或复合词的构造。二者之间唯一不同的是,由于各自文字系统的不同,中文传统字书是字–音(grapho-phonic)层面上的语文学,《八章》是音–形(phono-morphological)层面上的著作。需要指出的是,graph和grammar共同派生自希腊文词根γράϕειν,即grafein‘书写’。《八章》的内容仅有表法和名法,外加一点字法,而表法和名法又都说的是词的形态变化,那么精确地说,《八章》是古梵语的一部词形法著作。既然词形法属于文法的一部分,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八章》是半部文法。
唐箫雅同学引用《<本生谭>的诠释》(《普门学报》2001年第5期)一文的诠释,指出佛教本生故事如“千生舍眼”、“毗楞竭梨王身钉千钉”、“虔阇尼婆梨王剜身燃千灯”以及“尸毗王割肉贸鸽”等,生动展现了菩萨在成佛之前,为了利益众生而甘愿舍弃自身身体乃至生命的行为。这些故事不仅是佛教伦理观的具体体现,更是佛教修行理念的深刻表达。首先,这些故事体现了菩萨对众生的深切慈悲心。菩萨为了救助众生,甘愿承受极大的痛苦,甚至牺牲自己的身体,这种无私的精神体现了佛教中“无我”的理念,即超越个人的自我中心,关注他人的福祉。其次,这些行为是菩萨修行“六度波罗蜜”中的布施波罗蜜的具体实践。通过舍弃自身的身体,菩萨积累了成佛所需的福德资粮,为未来的成佛之路打下基础。此外,这些故事也强调了菩萨在面对苦难时的坚韧与毅力。菩萨不畏艰难,勇于承担痛苦,这种精神激励着佛教信徒在修行道路上坚持不懈,勇往直前。这些本生故事不仅是佛教教义的生动体现,也是佛教徒修行的榜样,鼓励信徒以菩萨为楷模,发大愿、行大悲、修大行,最终实现自利利他的目标。
黄凯老师对两位同学的汇报进行了评议。黄凯老师表扬了两位同学扎实的准备。鼓励二位同学将自身在阅读过程中获得的心得体会整理,并就自己感兴趣的点深挖进行专门研究。此外,要发挥自己专业的长处,运用世界史的视野,比较宗教学的方法,对世界各地不同宗教中结构性因素对比考察。也可以通过撰写研究史回顾或综述的方法,将相关的研究聚拢,线性研究佛教中国化、本土化的过程。谢志斌老师表扬了二位同学的进步。鼓励同学们使用跨学科的视野与方法来带动自己的研究。也希望同学们可以不吝惜自己的奋斗,将学术训练作为自己的锻炼,为自己的学业打好基础。
至此,“西北大学玄奘研究院读书会”第115期活动圆满结束。
(编辑:华也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