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9月23日晚7点,西北大学玄奘研究院第120期读书会在线上举行。本次读书会汇报的内容为于君方《观音—菩萨中国化的演变》一至六章,由历史学院硕士生周子菲和区域国别学院硕士生李瑶领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夏德美研究员评议。西北大学历史学院李永斌副教授、区域国别学院谢志斌副教授、陕西省社科院黄凯老师,以及西北大学历史学院、中东研究所、哲学学院、文学院及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四川大学、武汉大学等高校和单位60余名师生在线上一同参与了此次读书会。

首先由周子菲同学对《观音—菩萨中国化的演变》一至三章的内容进行汇报。周子菲同学汇报的内容分为三个部分,分别是导论、观音信仰的佛典出处以及中国本土经典与观音信仰。在第一章导论中,周子菲同学先论述了观音信仰的欧美注目与本土空白。观音信仰传入欧美后,受到美国女性主义学者的关注,引发了对观音“女神”身份的思考。这一现象促使我们重新审视观音信仰在中国的本土化过程。除了性别问题外,观音信仰在中国的本土化还涉及其在所有信奉佛教的国家盛行的原因、观音在中国的性别转变、观音信仰与中国地域文化的结合、观音功能的扩展以及观音与中国民间教派的融合等。观音的转变是佛教适应中国文化的微观缩影,通过观音研究可以窥探佛教与儒道文化的互动逻辑。接着,周子菲同学提到了观音信仰在亚洲扎根的双重原因。第一是印度观音的核心地位,印度是佛教发源地,观音是除佛陀外少数“历久不衰的大众信仰菩萨”,其梵文经典、艺术造型为亚洲其他国家提供了“正统范本”,降低了传播阻力。第二是佛教的文化适应性,佛教传入其他国家时不试图取代当地宗教,观音随本土文化调整名号与功能,如柬埔寨、越南称“Lokesvara”,缅甸称“Lokanatha”,斯里兰卡称“Natha Deviyo”,西藏称“Chenresi”。
周子菲同学又提到了观音在不同文化中的呈现,首先是中国及与中国历史文化相关的国家,将观音视为禅修者智慧典范(如禅宗观“观音耳根圆通”)与对妇女仁慈的“慈悲女神”(如救难产、送子嗣),具体表现为观音功能贴近民生(救水火难、免牢狱灾、满足求子愿),造像逐渐中国仕女化(白衣观音、鱼篮观音)。其次是斯里兰卡、西藏地区及东南亚,己视为观音化身(阇耶跋摩七世造“散臂世自在王”像,象征君主对众生的救度),西藏松赞干布赞普(7世纪)和达赖喇嘛(格鲁派认定)也被认为是观音化身,形成“宗教-政治”合一的统治合法性来源;这种关联的核心逻辑是“神王信仰(devaraja)”——君主借观音“普世估主”的身份,将世俗统治神圣化。周子菲同学谈论到菩萨与中国王权的关系,观音在中国未与王权产生关联,佛教传入前中国王权意识形态及象征已确立,如周朝“天命之说”(君主权力源于“天”,非神授)、汉朝儒家思想对王权理解的支配(董仲舒“天人感应”强调君主需“行仁政”,而非借宗教神化);虽有个别统治者借佛教证明统治合法性,但影响有限且不持久,极少有皇帝宣称是观音化身。北魏文成帝(452-465在位)造云冈石窟佛像,象征先皇功德,但不涉观音;武则天(690-705在位)自称“弥勒下生”,借弥勒信仰证明篡唐合法性,与观音无关;慈禧太后虽曾扮演观音拍照,但仅为娱乐,无政治目的。此外,儒家士大夫对“宗教神权”的警惕(如韩愈《谏迎佛骨表》反对佛教干预朝政),也阻断了观音与王权结合的可能。
关于民间观音信仰,周子菲同学特别提到了许理和《佛教征服中国》,汉代佛教被接受并非因与本土传统相似,而是因其“新奇”,是“外来的另类选择”——汉代儒家强调“入世伦理”,道教侧重“长生修仙”,而佛教“生死轮回”“普世救度”提供了全新的精神维度。周子菲同学并对观音融入中国本土的原因进行了介绍。观音作为充满慈悲、普门示现的救度者,其能力是中国本土诸神所无(如西王母管长生、土地神管地方,均无“普世救苦”功能),填补了当时中国宗教的空白;且被接纳后,中国人以中华文化模式理解这位菩萨,如用“家庭伦理”重构观音身世(妙善公主传说)、用“感应宇宙观”解释观音救度(信徒“诚心”与观音“回应”的互动),其转变可视为佛教汉化的个案,与禅宗融合老庄、净土宗简化修行法门等汉化现象一脉相承。周子菲同学对印度的观音菩萨信仰、以及从“佛教在中国”到“中国佛教”的历史概述进行了介绍,并对于君方《观音—菩萨中国化的演变》一书的研究方法进行了总结。大乘佛教中观音是“天上的”或“宇宙的”菩萨(Mahasattva,大士),已达菩萨道最高阶位第十地,是慈悲的圆满化身,与文殊菩萨(智慧象征)、普贤菩萨(行愿象征)并称“三大士”,且如《悲华经》《大乘庄严宝王经》所述,观音发愿“度尽众生方成佛”,其“大悲”特质区别于其他菩萨。从初期(2-5世纪)僧团部分僧侣礼拜对象(绍本认为秣菟罗碑铭显示观音与“释迦比丘”团体相关),逐渐成为僧、俗二众信奉的独立神祇(五世纪后造像增多,如伊罗拉地区观音像达110件,为其他菩萨三倍),直至12世纪佛教从印度消失前仍盛行(波罗王朝密教观音像为普世救度者,如那烂陀石碑“观音救饿鬼”像)。
佛教由中亚人和印度传法僧沿丝路(南道:于阗、龟兹;北道:疏勒、焉耆)在汉朝后半叶(约公元前1世纪)传入,最早的文献记录是《后汉书·楚王英传》载“英喜黄老,学为浮屠斋戒祭祀”;最初中国人对佛教理解贫乏,如将佛陀与黄帝、老子共祀,认为佛陀是“能授长生术的神明”,佛像创作曾以西王母像为范本(四川乐山麻浩、柿子湾墓砖浮雕佛像,二世纪晚期,位置与西王母像相同,象征天界)。汉魏六朝时期(220-589)佛教逐渐确立,与道教相互竞争又相互借鉴。隋、唐时期(581-907)中国本土宗派创立。唐代密教经典翻译(善无畏、金刚智、不空译《十一面观音经》《千手经》等)促进观音圣像制造,寺院中出现十一面、千手千眼观音像(如长安七宝台703年十一面观音石雕)。宋代后观音逐渐女性化,本土观音像(水月观音、白衣观音)陆续出现(杭州烟霞洞940-949年白衣观音像,现女相);各地形成观音朝山圣地(如浙江普陀山、四川峨眉山),“地域化”成为观音本土化的进一步发展(如普陀山与“不肯去观音”传说结合,成为观音道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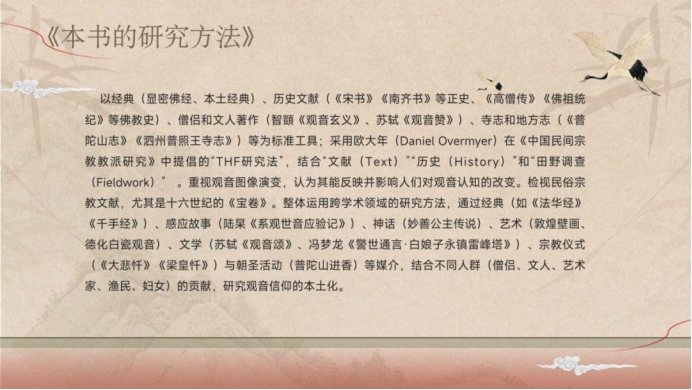
在第二章观音信仰的佛典出处中,周子菲同学先对观音角色的演变进行了介绍。观音最初仅作为佛陀或其他菩萨的随侍,无独立作用,如在《成具光明定意经》中是三十位“明士”胁侍菩萨之末。观音受佛陀嘱托,为众生开示“持名、持咒感应法门”,如《法华经·普门品》中,佛陀解释观音“观世间音声而度脱”。观音受佛陀嘱托,为众生开示“持名、持咒感应法门”,如《法华经·普门品》中,佛陀解释观音“观世间音声而度脱”。观音脱离对其他佛、菩萨的依附,成为宇宙级救度者,兼具创造、救苦、赐福功能,如《大乘庄严宝王经》称其“宇宙创造主”。周子菲同学并从佛的胁侍菩萨之一、后继阿弥陀佛的未来佛、众生的救度者、普世救度者对观音的角色进行了详细的解释。观音最初的身份是胁侍菩萨,作者提及了“观音”的来源以及观音信仰产生的缘由,这不仅体现在经典的文本表达上还体现在艺术作品中。最早以“观音”之名提及该菩萨的汉译经典是185年支曜译的《成具光明定意经》(属般若经群),经中三十位名为“明士”的胁侍菩萨中,观音是最后出现的一位。阿弥陀佛与观音菩萨之间的关系,不仅可以从经典表达中体现还可以通过经典的用词中体现。几部早期汉译经典以观音授记成佛为主题,如453年于阗沙门昙无竭(Dharmodgata)译的《观世音菩萨授记经》。赞颂观音菩萨的核心经典包括《法华经》《观无量寿佛经》《首楞严经》等。《法华经》先后六次汉译,现存三个译本,竺法护286年译的《正法华经》(最早译本)称菩萨为“光世音”(Abhalokasvara,意为“光照世间音声者”),救度世人免于七种危难(火难、水难、风难、刀难、鬼难、枷锁难、怨贼难),解脱贪、瞋、痴三毒,且使不孕妇女生儿育女,经中载“闻光世音名,火即寻灭、水不能溺”。浩特在《宝冠中的佛陀:观音信仰的起源与发展》(Buddha in the Crown, 1991)中认为《大乘庄严宝王经》成于四世纪到七世纪之间,且其使用的梵文本与汉译本可能存在差异(梵本强调“观音降魔”,汉本侧重“救度”)。经中描述观音向阿鼻地狱、饿鬼大城众生宣说佛法,释迦牟尼佛在祇树给孤独园修“一切清净”禅定,出大光明,除盖障菩萨问因,佛告“此光来自观音,正向阿鼻地狱众生说法”,地狱猛火灭、变为莲池;观音又往饿鬼大城,身上毛孔出水,解饿鬼饥渴,令其省悟“贪造恶业堕恶趣”,转生阿弥陀佛净土;还提及观音前世为圣马巴拉哈(Balaha)救辛哈喇王子(Sinhala)的故事。
在第三章中国本土经典与观音信仰中,周子菲同学先介绍了观音相关佛经抄本,《白衣大悲五印陀罗尼经》与三卷明代抄本,其中三卷明代抄本分别是《佛顶心观世音菩萨大陀罗尼经》、《佛顶心观世音菩萨疗病救产方大陀罗尼经》和《佛顶心观世音菩萨救难神验大陀罗尼经》。又介绍了若干颂扬观音的重要本土经典,《观世音菩萨往生净土本愿经》、《佛说观音三昧经》和《高王观世音经》。周子菲同学提到了唐代以来流行的两组陀罗尼经群,陀罗尼是密教经典不可或缺的要素,梵文“dharani”的音译,意为“总持”,即浓缩佛经要义的咒语,被认为“具有神验力”;与正统密教经典不同,本土陀罗尼经的念诵通常是唯一要求,无需复杂仪轨(如结界、火供、手印)。周子菲同学又提到公认为明代皇后所撰述的两部本土经典为《大明仁孝皇后梦感佛说第一希有大功德经》与《佛说大慈至圣九莲菩萨化身度世尊经》。
最后,周子菲同学又分析了几个问题,一是唐代观音女性化的动因,从政治文本的影响看,武则天通过《大云经神皇授记义疏》等政治文本,将自己塑造为“弥勒下生”的女性统治者,这一策略直接推动了观音形象的女性化。从经典依据的支持看,《法华经·普门品》“应以女身得度者,即现女身而为说法”的教义,为观音性别转化提供了理论依据。从女性信众的推动看,唐代女性信众将观音信仰与个人情感结合,比丘尼群体主导的观音造像刻意弱化男性特征,强化女性化细节。二是宋元观音造像的世俗化分析,观音世俗化的核心动力之一,是感应故事的广泛传播与生活化叙事。这类故事以真实人物、确切时空的危难经历为核心,如救水火难、脱牢狱灾、治疑难病等,均对应民众日常面临的生存困境——从敦煌文书中的民间信众“称名免溺”,到后世感应录中“祷观音愈癌”“避战乱得安”,故事主角涵盖渔民、囚徒、妇人等各阶层,打破观音作为“经典神祇”的距离感。同时,故事传播依托宝卷、戏曲、口头讲述等通俗媒介,如《高王观世音经》相关的孙敬德“刀折免死”故事,经民间戏曲改编后深入市井,使观音从“需研读佛经才能认知的菩萨”,转变为“能即时回应世俗苦难的护佑者”,成为民众应对生活风险的精神依托。三是《法华经·普门品》“多化身救度”阐释的历史演变分析,在经典依据与化身类型上,明确《法华经·普门品》(鸠摩罗什译本)是核心经典,其“应以何身得度者,即现何身而为说法”的表述形成“三十三身”,涵盖佛身、辟支佛身、声闻身、天身、人身、妇女身、童男女身、八部身及执金刚身。在本土化演变倾向上,提出印度观音化身多与印度教神话、宗教宇宙观相关(如梵王、帝释),而中国观音化身逐渐剥离印度本土元素,且宋代后女性化身占比提升。在信仰实践与化身关联上,指出感应故事中观音常以僧人相、白衣人相等化身示现,早期多为男性形象(如竺法义梦中观音现沙门像为其治病),后期逐渐出现女性化身;同时强调信徒所见化身形象受当时观音造像影响,而化身示现经历又推动新造像创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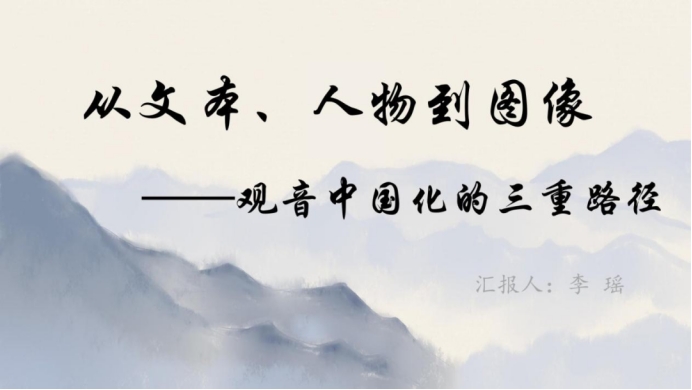
接着,李瑶同学对《观音—菩萨中国化的演变》四至六章的内容进行汇报,题目为“从文本、人物到图像——观音中国化的三重路径”。李瑶同学先对第四章感应故事与观音的本土化的内容进行介绍,这一章主要探讨“感应故事”在观音信仰本土化进程中的核心作用。作者指出,这类故事并非简单的“神迹”记录,而是基于中国固有的“天人感应”宇宙观,为观音的救度能力提供了本土化的理解框架。早期感应故事(如《光世音应验记》)由士大夫阶层记录和编纂,其主角涵盖社会各阶层,显示了观音信仰广泛的群众基础。故事中,观音最常见的救难场景(如免于火难、水难、刀兵狱难)与《法华经·普门品》的描述相呼应,但叙述方式和文化逻辑则是中国的。此外,感应故事与观音圣像之间存在密切的互动关系:信徒的经历受既有图像影响,而新的灵验故事又反过来促进新图像(如女性化的白衣观音)的创作和流传。
在第五章神异僧与观音的本土化中,李瑶同学介绍到本章分析了另一条观音本土化的路径:将历史上具有神异能力的僧人(神异僧)塑造为观音菩萨的化身。作者以宝志和僧伽两位著名神僧为案例,详细论述了他们如何通过传记、传说逐渐被神化为观音(尤其是密教形象十一面观音)在人间的应化身。这一过程将一位抽象的、外来的菩萨,具体化为与中国历史、地域(如僧伽与泗州信仰)紧密相关的“本土”神圣人物。神异僧信仰强化了观音的救度者形象,其神异故事的功能与感应故事类似,但更侧重于通过具有卡里斯玛的个体来展现观音的威力,从而在民间获得更广泛的接受和崇拜。
在第六章本土图像与观音的本土化中,李瑶同学称本章从艺术史角度,探讨了两种在中国创造并流行的观音图像——水月观音和白衣观音——如何参与并体现了观音信仰的本土化与女性化进程。这些图像缺乏直接的印度经典依据,其灵感源于中国本土的文学想象、艺术创作和宗教实践。“水月观音”以其文人化的诗意美学体现了禅与净土的融合;“白衣观音”则与民间祈求嗣息(求子)的信仰结合,逐渐强化了其女性慈母的形象。这些图像不仅是艺术创作,更是信仰和教义的视觉表达,深刻影响了中国民众对观音的认知。李瑶同学提出观音被中国文化所接受和改造,具有本土化和女性化的特征。并介绍了观音中国化的三重路径,一是感应故事,感应故事中描述了神异僧的灵验,在文本层面提供了叙事的合法性和传播的活力。这些故事深深植根于中国的“天人感应”思想,特别强调了感应故事与观音图像的密切关系,许多故事中观音显灵的形象源于当事人当时所能见到的观音造像,新的灵验故事又反过来刺激和催生了新的观音像的创作。二是神异僧传说,神异僧的传说促进了其圣像的创作与崇拜,在人物层面提供了身份的具象性和地域的归属感。核心功能是提供具象的崇拜对象,比如,宝志(志公禅师)是南北朝时期的神异僧,以其预言和神迹著称,被后世认定为观音应化身。僧伽大师是唐代僧人,在泗州(今江苏境内)建立道场,被尊为“泗州大圣”。他因其巨大的感召力和神异能力,死后被官方和民间共同认可为观音化身。他的存在,使观音信仰与中国特定地域(泗州)紧密结合起来。三是本土图像,新的观音图像又成为新的感应故事的灵感来源,在视觉层面提供了最终的美学定型和性别的转换。核心功能是视觉定型。这两种图像是纯粹的中国创造,代表了中国人对观音的独特理解。水月观音出现于唐代,呈现一位悠闲、沉思的菩萨形象,背景是竹林、流水和明月。白衣观音通常为女性形象,身着白衣,恬静慈祥。其信仰核心常与“送子”相联系。白衣观音彻底展现了观音作为生育和保育女神的职能,是其女性化和民俗化的关键一步。
夏德美老师对两位同学的汇报进行了评议。夏老师首先肯定了读书会的组织形式和两位同学的汇报,强调了问题意识在学术研究中的重要性。接着,夏老师指出周子菲同学所提到于君方《观音—菩萨中国化的演变》一书中佛教传入时间上的疑惑与看法。夏老师又讨论了佛教与王权的关系,强调中国政教关系的独特性。中国政教关系是研究宗教时需重点考量的议题,其呈现出鲜明特点。佛教传入中国后虽影响较大,但在与政治权力的根本关系上,整体始终处于王权之下,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特征。南北朝时期是特殊阶段,南方高僧讲法时皇帝曾匍匐在地,沙门一度不敬王者,如慧远的相关主张有一定影响力。这一方面因当时南方王权尚处上升期,受门阀士族限制,权威不足;另一方面南北对峙局面使南北方政权集权专制程度较弱,佛教得以拥有相对自由空间,像庐山可在南北政权间保持一定游离状态。然而,隋唐大一统中央王权建立后,佛教再难维持不敬王者的状态,逐渐被纳入王权体制。若跳出西方有组织宗教的定义范畴,中国传统社会可视为“政教合一”,此处的“教”指儒家之教或董仲舒提出的“天人感应”体系。皇帝身为“天子”,集王权与神权于一身,既是神圣秩序在人间的代表,又是人间秩序的最高掌控者,
具有神圣性。即便王朝更迭时,前代帝王因荒淫暴虐被推翻,新政权仍需前代皇亲 “让位”,正是因为皇位被认为是上天选定的,具有神圣性,即便某任帝王失去上天信任,皇位本身的神圣属性依然存在。
然后,夏老师认为李瑶同学所提出的观音的本土化和女性化非常具有问题意识,尤其强调观音传入中国之后女性化转变的问题是研究观音信仰的核心所在,分析了观音女性化的可能原因,包括唐代女性地位较高和天人感应思想的影响。观音女性化是值得探讨的话题,西方女性主义者关注观音女神形象,但不能简单以此认定中国女性地位高,其女性化或与唐代历史背景相关。儒家礼制下,女性受三从四德、女戒等约束,但中国女性地位并非一成不变。隋唐以前女性地位相对较高,如谢道韫等才女活跃,北魏冯太后、唐代武则天等女性登上政治舞台,不少高贵出身女性在文学领域留下印记。而明清后,女性逐渐被束缚于家庭,地位下降,留存姓名者多为秦淮八艳这类特殊阶层。唐代作为观音女性化可能的关键时期,其相对较高的女性地位,与观音在民间信仰中逐渐占据重要角色的现象之间,或许存在值得探究的历史关联。
谢志斌老师进行了总结,他先向夏老师介绍了读书会的两种类型,读原典和读学术著作,并强调了观音信仰研究在佛教中国化中的典范意义。关于观音女性化的原因,谢志斌老师总结为两点,一方面的原因是在这个印度本土和佛教内部的原因。另外一个就是外部原因,也就是中国文化、中国环境、中国人的心理等。最后,谢志斌老师鼓励同学们通过读书启发思考,形成自己的观点,写出论文,也是读书会很有价值的地方。
至此,“西北大学玄奘研究院读书会”第120期活动圆满结束。
(编辑:华也靓)